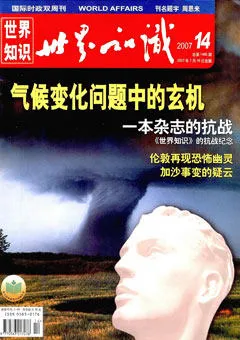一本杂志的抗战
2007-12-29胡孝文
世界知识 2007年14期
上篇:胡愈之和金仲华的“流浪”
金仲华:带着“世知”流浪
流亡第一站:武汉
1938年1月的武汉。
作家池莉在《老武汉——永远的浪漫》一书中生动地写道:
(南京沦陷后,)全国各界的名人和精英们自然都聚集到了武汉。全国抗战大同盟总部成立。中华抗日救亡总会成立。中华全国文艺抗日协会成立……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在武汉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就有80多个,创刊或者出版的报刊有75种。老武汉热忱地全力投入了抗战。……人民群众在举行大会,在呐喊,在歌咏,在捐献。国家的首脑们在大楼里紧张地开会。全国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随处可见……

当时,在武汉出版的刊物,就包括《世界知识》,随处可见的文化界人士中,就包括《世界知识》的负责人金仲华,他是与生活书店的主持人邹韬奋一起来到武汉的。
武汉是已在上海战斗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世界知识》战时流亡的第一站。从1938年1月1日起,《世界知识》开始在武汉出版。尽管战时的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对于新闻杂志出版而言困难重重。《世界知识》与生活书店的员工们组成了以邹韬奋为首的阵容强大的编审委员会,金仲华为副主任,其他委员有胡愈之、范长江、钱俊瑞、柳湜、张仲实等新闻出版界名流。委员会决定: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全国各地,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业务,力争在中等以上的城市建立生活书店分店。
在战争环境里,条件非常艰苦。两份享有很大声誉和影响的刊物——《世界知识》与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编辑部,就同挤在一个很窄的套间里。那时候,这两份姊妹刊物的办刊方针是他们俩一起商定的。
“孤岛”岁月
半年前,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作为“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还在国民党当局的监狱里。而被公推代理韬奋担任其主编的《生活星期刊》负责人的金仲华,一直在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营救“七君子”的运动。1937年7月31日,即芦沟桥事变爆发20多天后,“七君子”获释出狱。在全面抗战的形势下,金仲华与邹韬奋、《世界知识》与生活书店的密切合作,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金仲华是从1937年4月1日起,继胡愈之、张仲实、钱亦石、钱俊瑞之后,责无旁贷地担任《世界知识》主编职务的。当时他也没有想到,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他竟带着杂志从上海转到武汉、广州、香港、桂林,历时四年,在流亡中坚持出刊,创造了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迹。抗战胜利后他从重庆回到上海,又领导了这份杂志的复刊。
抗战爆发后,金仲华把整个篇幅都用在了宣传抗日救亡、团结抗战上。而且,他公然介绍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展开的敌后游击战成果。他还在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上撰写《战局一览》,每期一篇。此外,他参与负责向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组织发送稿件的“国际新闻供应社”的工作。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英法当局顶不住压力,进步文化界遭受愈加严重的打击。很多报刊相继停刊。《世界知识》与生活书店旗下的另外几本刊物,如《妇女生活》、《国民周刊》等曾经合在一起,出版战时联合旬刊,但只出版了四期,就无法继续下去。
于是,金仲华和邹韬奋决定转战内地,继续宣传抗战。年底,两人带领《世界知识》和生活书店,一同开始了战时的流亡历程。此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失陷,他们与文化界许多人一样迁往武汉。在旅途中,他们顾不上劳累,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抗战宣讲。与此同时,《世界知识》一部分尚未离开上海的编辑和作者,在胡愈之的安排设计下,又出版了一本名为《集纳》的周刊,由胡愈之二弟胡仲持主编,同样向读者介绍国际形势。但它只出了九期,也被租界当局查禁了。而胡愈之就是以这些原《世界知识》的人员为主,组织翻译了斯诺的《西行漫记》。
广州:只出了三期
《世界知识》在武汉一共出版了12期。
战事如云。恶化的局势不给他们更多的时间。1938年6月,长江马当封锁线被日寇突破,武汉局势马上紧张起来。敌机疯狂地向武汉三镇倾泻炸弹,政府机关忙于撤退,工厂商店纷纷停业,难民潮似的涌来涌去,一切显得不可预测。金仲华和邹韬奋坚持着,直到根本没有出版条件时,一行人才在7月5日被迫转移。邹韬奋率书店总管理处远赴陪都重庆。考虑到《世界知识》需要经常搜集外报外刊的资料,金仲华决定南下广州,继续出版《世界知识》。他们一路上避开日机轰炸,火车白天不能开,晚上也常常停驶,三四天后才到达广州。战时广州的条件更差,金仲华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工作室,只好在生活书店分店会客室的一个角落里工作。但只出了三期,广东却也呆不住了——正当武汉外围激战的时候,日军突然进犯广东……内地无处可去,只有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尚是个安全的地方。1938年8月,金仲华一行转移到香港。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
因他们,香港“沙漠变绿洲”
在内地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文化界人士纷纷来到香港。一个曾经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就是这样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从而成为“继北平、上海以后的中国文化中心地”。
但是,在香港出版杂志,必须有港英当局的许可证。《世界知识》按照规定去申请,只因找不到有权势者出面疏通,领不到证,怎么办?但金仲华依然决定,“先出再说!大不了封门坐牢”。所以,当时的《世界知识》版权页上仍旧印着在武汉、广州出版,但在编辑室一栏中告知读者,如有信件或稿件,请寄就近的生活书店转来。多年之后,金仲华提起此事,笑道:“我在香港编过一段时间的地下刊物。”
正在无路可走之际,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的华侨巨富胡文虎父子急需有能力打开局面的办报人才。于是,金仲华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廖承志推荐,做了《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就势通过胡氏父子的关系打通“关节”,办到了《世界知识》的出版许可证,并得到允诺,由《星岛日报》印刷厂承印《世界知识》。这样,《世界知识》就成为香港“合法”的出版物了。金仲华就这样一手抓《星岛日报》,一手抓《世界知识》。是年,他31岁。
金仲华接手《星岛日报》后,花大力气进行了整顿。他请挚友郑森禹、刘思慕、乔冠华、张铁生协助主持《世界知识》的工作,自己有段时间则全身心投入到《星岛日报》上。他邀请抗日立场坚定、学识丰富的邵宗汉担任副总编辑、国内外著名的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人专栏编辑、名作家戴望舒任副刊编辑。经过整顿,报纸面貌为之一新,发行量与日俱增。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离重庆,当了汉奸。于是,整顿后的《星岛日报》就成为金仲华宣传抗日、怒斥汉奸的重要舞台。1940年7月,汪精卫以所谓“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身份,发布伪“通缉令”,被通缉者83名,金仲华也名列其中。对此,金仲华一笑了之。
1939年3月,国民党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山西与陕甘宁边区多次发生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寻衅事件。这让金仲华非常不安。他在《星岛日报》发表《几种危险征象》的社论,“最近国内党派间的团结,特别使人焦虑。虽然大家都知道必须加紧团结,才能打破日本、汉奸政治进攻的阴谋。”当1941年1月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发生后,金仲华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将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在《星岛日报》刊登。接着,他又连续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种种图谋的文章。这就致使国民党驻香港的海外部对金仲华恨之入骨。在“最高当局面谕”压力下,胡氏父子要求金仲华转变态度,遭到拒绝。其后,金仲华的工作受到限制。1941年6月,金仲华、邵宗汉、羊栆等辞职,完成了他们在《星岛日报》的使命。
桂林停刊
1942年1月8日晚,一条渔船在夜色中悄悄离开香港。船上的人都是当时和后来中国文化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夏衍、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金仲华也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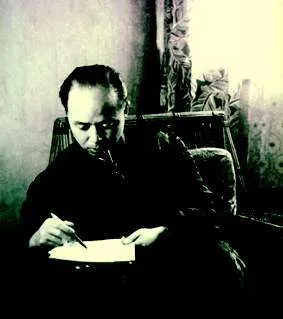
在香港,《世界知识》坚持了两年半。1941年12月7日,风云骤变。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快,日军进占香港,所有的进步报刊全部无法生存,抗日的文化人更是成为日军搜捕的目标,不得不暂时隐蔽起来。《世界知识》杂志的所有资料、图版也全部损失。在中共精心安排下,金仲华等一批文化界知名爱国人士离开香港。那条渔船就是负责秘密将他们转移出去的。他们被营救到广东东江纵队的游击区。次年2月,金仲华去了文化界聚集的后方桂林。他原拟在那里继续出版《世界知识》,但遭到国民政府的禁止而未能如愿。这是《世界知识》历史上的第一次被迫停刊。金仲华还在各种报刊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还一度担任广西日报编辑,经常应邀在各团体和学校中作形势报告,宣传抗日。1944年11月,华南日军扑向桂林,于是,金仲华又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受聘担任美国新闻处译报部主任。其间,他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将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等重要文件,通过“美国新闻处”电台向世界广播。此外,他还投入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工作中去。其实,金仲华在香港时就一直参与“保盟”活动,并成为宋庆龄的有力助手。1941年3月,宋庆龄出版《“保盟”通讯》中文版,请邹韬奋、金仲华负责,宋庆龄的许多文章,都是由金仲华完成中译稿的。
胡愈之:南洋岁月
受周恩来直接安排
在金仲华带领《世界知识》一路在流浪中继续出刊的同时,胡愈之在上海沦陷后也离开了这里。他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辗转武汉、长沙和桂林,进行抗战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是胡愈之在上海认识的并影响他一生的关键人物。而周恩来后来也与《世界知识》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愈之是《世界知识》的创办人,但抗战前,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他,离开了《世界知识》,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中来。抗战时期,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他悉心组织、翻译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编印《鲁迅全集》等震撼人心的杰作。
在桂林,周恩来将胡愈之介绍给白崇禧,要胡做白崇禧的秘书,但遭到蒋介石的激烈反对。胡愈之便到白崇禧挂名的广西建设委员会任职。很快,他与广西上层人物建立了关系,并兴办文化供应社。这个文化供应社成为桂林团结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活动的大本营。但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实行限共、防共、融共政策,并将大量中央军开进广西,迫令白崇禧一起反共。不久,在获知胡愈之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之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将胡愈之撤出桂林,向香港转移。临行前,胡愈之以轻松口吻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但他没有料到,等待他的是一个全新的战场——南洋,并且一去就是八年。
转战南洋
南洋,是华侨主要聚居地,也是抗战时期支援中国内地抗战的重要阵地。当地华侨在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踊跃参与到中国大陆的抗战中来。但当时华侨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分歧认识不清,为了使南洋华侨认清国民党真面目,最大限度地支援抗战,中共中央指示要加强对南洋华侨的宣传工作,扩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范围。正巧,当时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正物色办报人才,于是周恩来推荐了正在香港的胡愈之。这个消息是通过廖承志传达的。
胡愈之南洋之行困难重重。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英法当时对日本采取“绥靖”措施,并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关闭了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滇缅公路,而且严格控制内地与南洋的人员往来。由于胡愈之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物,在周恩来要保证胡愈之的绝对安全的指示下,经多方筹划,胡愈之决定蒙混过关。
当时中国大陆到南洋的轮船分三等,一、二等船舱的旅客须要随带护照、交纳大陆有关方面开出的证明,到达目的地后还要到指定的地点接受严格的审查。为保证胡的安全,廖承志决定让胡愈之坐三等舱走。廖承志立即发电报给周恩来告诉胡的一切行程事宜,得到周的批准后,廖承志和胡愈之开始安排上路的一切准备。胡愈之使用的是“胡学愚”的名字(他的原名),廖承志找人托关系疏通了胡所乘船的船医,偷偷塞给他一百大洋。这位船医胡乱给胡开具了身体健康的证明,免去了例行检查,这样胡愈之安全抵达新加坡。
1940年12月2日,《南洋商报》头条刊出了胡愈之等人的聘任消息,并刊出巨幅照片。这让英殖民当局大为吃惊。胡愈之,这个黑名单上的危险人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新加坡的华民政务司立即传讯胡愈之,胡愈之坦然递上印有“胡学愚号愈之”的名片,他说:“因报社催我到职,所以来不及办护照,就坐三等船来了,但我体检合格,是合法入境。胡愈之是我的别号,中国人的习惯在正式场合用名不用号的。”检查没有漏洞,而胡愈之的解释又合情合理,让英殖民当局无奈何。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派的身份主编《南洋商报》。履新伊始,胡愈之便对症下药,决定改变该报的办报方针,增加抗战宣传方面的内容,加强报纸的评论工作。胡愈之除每期写专论外,还亲撰“星期专论”。1941年1月,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胡愈之大胆刊登《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关于皖南事变访问记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接着又亲自写出《团结则存,分裂必亡》的社论,充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内战的可耻阴谋。在日本与德意形成三国同盟并大举向南侵略、南洋局势岌岌可危之际,胡愈之又在《南洋商报》上公开提出了“援助中国抗战,加强英美合作,厉行对日禁运,实行远东民主”四个法宝。这些分析振聋发聩、轰动一时。
与陈嘉庚“相恨见晚”
1941年是胡愈之在南洋开展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胡愈之见到了南洋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富有强烈的爱国心,但当初对国、共两党缺乏清醒认识。1940年底他先后访问了延安和重庆,并同毛、蒋接触后,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国统区民不聊生、国民党腐败无能尤感愤懑,并公开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断言。
尽管胡愈之此前与陈嘉庚并未谋面,但两人一见如故、相恨见晚。与胡愈之的交往,使陈嘉庚的思想“赤化”,更加坚定地站到了中共的一边,这自然引起国民党的忌恨。蒋介石派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到新加坡拉拢陈嘉庚。面对国民党的笼络,陈嘉庚一笑了之。

这一年在南洋,胡愈之找到了自己“久违”的爱情——他与有“进步文化界少有的女秀才”称谓的沈兹九结成连理。据沈兹九回忆,她来新加坡之前,受周恩来指派的廖承志曾对她说:“你去新加坡,主要是帮助胡愈之开展工作。”可见,胡沈的婚姻,也是周恩来促成的“天作之合”。当时,胡45岁,沈43岁。
与郁达夫一起“逃亡印尼”
郁达夫是1938年底应《星洲日报》之邀来新加坡宣传抗日的。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胡愈之以自己的卓越的组织能力,在很短时间内组织了以郁达夫任团长、自己为副团长的“星洲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和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
正当胡愈之和郁达夫并肩作战的时候,此前自诩新加坡是“坚不可摧要塞”的英国人投降了。于是,胡愈之夫妇、郁达夫、王任叔(即著名作家巴人,建国后任我国驻印尼大使)、汪金丁(建国后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家四口等,搭乘一支几米长的摩托舢板渡过马六甲海峡,逃到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
但是,印尼也很快沦陷了。他们决定向苏门答腊岛中西部进发,并隐姓埋名,改换职业隐匿下来。最终,他们在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地方落脚。这是个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偏僻小镇,就由于一群中国文化人的到来和后来郁达夫失踪遇害,而在日后闻名于世。
汪金丁的女儿汪雅梅,在《跟随胡愈之伯伯南洋逃难》一文中写道,在逃难的文化人中,胡愈之是主心骨,包括郁达夫在内,大家有事都向他请教商量。他处变不惊,组织大家学习印尼语文,研究印尼社会、历史和文化。后来汪金丁向他建议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的组织,得到采纳。
为不暴露身份,胡愈之剃掉胡须,化名张尚福,沈九兹化名张赵氏,郁达夫则成了妻舅,化名赵德清,并蓄起了胡须。为了维持生计,胡愈之决定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由郁达夫做老板,胡愈之自任会计。郁达夫是因为去镇上访问一位侨领时被日本宪兵发现会讲日语而被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的。胡愈之就以郁达夫的这点“优势”办下了营业执照。办厂,既能帮助一部分文化人解决生活困难,又能增加日军翻译郁达夫身上的保护色。后来他们还办了个肥皂厂。1943年二三月间,郁达夫装作害肺病,买通日本医生开了证明,才从宪兵处获准辞职。
酒厂销路不错。据汪金丁回忆,胡愈之每天上午都去酒厂,经常穿着一件短袖线衬衣和一条长裤、拖鞋,完全一副商人模样。而且,他极少到公开的场合露面。他曾穿着一件整洁的西装到印尼人的书店里买书,结果没等到他从书店里出来,却看到不少商店门上挂起了太阳旗,原来印尼人把他视为日本人中的大人物了。
1945年2月,郁达夫的身份被告发。日本人知道他是中国著名作家,怀疑他是联军间谍。郁达夫建议胡愈之等赶快离开。胡愈之建议分头疏散。胡愈之夫妇去了棉兰山区,张楚琨等则到了巨港。正是在此Q3rzjz5IGbTqHISQuoSokD4Gyxsg2gxP7+i+BypRGuY=期间,国内有了胡愈之病逝海外的讹传。
胡愈之是在印尼的报纸上知道日军失败消息的。但就在和战友们互庆余生之际,他收到了汪金丁打来的电报:郁达夫失踪了!胡愈之惊呆了。原来,郁达夫是8月29日傍晚被一个当地青年叫走而失踪的,当时他还穿着睡衣和木屐。在妥善安置郁达夫家属后,胡愈之要求联军机构查究郁达夫的下落。一年后,联军证实,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胡愈之迅速写出《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的长文,凭吊郁达夫并指出日军杀人灭口的嫌疑。建国后,他又托出任首任驻印尼大使的巴人对郁达夫之死进行调查,但未能如愿。所幸在胡愈之逝世前的1985年,经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1945年9月23日,胡愈之一行离开印尼,回到新加坡。他本想返回国内,但鉴于国内局势紧张,胡愈之又在党的指示下坚守南洋,从事出版和统战工作,直到1948年回到香港。此后,他由香港经上海到了解放区,并依途中所见,在西柏坡面见毛泽东时作出了全国解放的时间“不到两年”的估计,从而改变了毛泽东(毛当时估计“还有两年”)的时间表。事实证明,胡愈之的预见是正确的。
(本文图片均为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