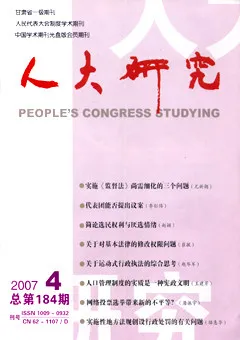实施性地方法规创设行政处罚的有关问题
2007-12-29骆惠华
人大研究 2007年4期
根据立法法第六十四条有关立法权限的划分,地方性法规包括三类:即针对地方性事务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针对中央专属立法权之外、中央尚未立法的事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执行已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地方性法规。由于前两种没有直接上位法,理论上把它们统称为创制性地方法规,而把后一种叫做实施性或执行性地方法规。
从实践上看,创制性地方法规在整个地方性法规体系中所占比例较小,在行政处罚设定方面也没有太大争议。本文仅就实施性地方法规中创设行政处罚的有关问题做一探讨。
一、实施性地方法规可否创设行政处罚
所谓实施性地方法规创设行政处罚,就是指实施性地方法规在直接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之外,增设新的行政处罚。关于实施性地方法规可否创设行政处罚,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分歧的原因在于对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不同理解。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否定论者认为,该规定从行为、种类和幅度三个方面,对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问题进行限制,其中,有关“行为”的限制就是明确否定地方性法规创设行政处罚。因此,实施性地方法规只能对其上位法设定的行政处罚在种类、幅度等方面进行细化,作出更加具体可操作的规定,而不能扩大上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范围,另行增设新的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肯定论者则认为,实施性地方法规对于其上位法已设定的行政处罚可以细化,自不待言。但对于上位法没有规定的违法行为,也可以作出补充规定并增设相应处罚。
笔者同意肯定论者的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并未明文禁止实施性地方法规在上位法既有规定之外另行设定行政处罚。“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按照语言逻辑,如果地方性法规不是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作出具体规定,而是在法律、行政法规的既有规定之外另行“设定”行政处罚,就不应该受“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的约束。否定论者忽视了语言内部的逻辑关系,曲解了条文的含义,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条文本身并没有界定所争议的问题。
其次,实施性地方法规创设行政处罚是我国立法实际状况的需要。第一,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中,有不少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于改革开放之前或改革开放的初期,甚至有些建国初期的法律至今仍然有效。如《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城市集市贸易管理办法》等,均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税条例》《户口登记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 等,则制定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立法时的社会背景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已大不相同,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就行政处罚方面而言,当时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或适应现在行政管理的需要。第二,历史上,我国的立法活动一直贯彻着“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许多法律、行政法规只是框架式的或粗线条的,有关行政处罚条款的设计自然也是粗略的,并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区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第三,立法者的认知水平总是有限的,并非全知全能。任何立法都必然打上立法者认知水平的烙印。因此,在立法中,对某些领域、某些环节考虑不周,遗漏某些事项、细节,是难免的。还有,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差异较大,在一地存在或突出的问题,在另一地方则不一定存在或突出。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者必须站在全国的角度,通盘立法,这就难免忽视甚至舍弃局部,使得各地的实际问题并不都能反映到全国的立法上。总之,上述种种因素综合导致了法律、行政法规在设定行政处罚条款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包揽无遗,为了适应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地方性法规必须对法律、行政法规进行补充。否则,地方性法规本身存在的意义也会成为问题。
再次,从关联条文的理解和实际运用看,实施性地方法规也可以创设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此条是对实施性行政法规(即为实施法律而制定的行政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限制。不难发现,它与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表述方式完全相同。相同的表述应作相同的解释。那么,是不是实施性行政法规也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而另行创设行政处罚呢?我们还是先看两个例子。《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9年1月1日实施)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逾期不恢复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耕地复垦费二倍以下的罚款。”该条对“不恢复种植条件”的违法行为设定处罚,就是一种创设规定,其上位法《土地管理法》并没有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规定,更没有设置处罚。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发布并实施)第四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将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改变为其他林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收回经营者所获取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并处所获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三倍以下的罚款。”该条“将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改变为其他林种”的违法行为,在其上位法《森林法》中也未作规定,同样属于创设的行政处罚。这样的例子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中还可以找到很多。既然实施性行政法规可以“突破”法律的规定,创设行政处罚,那么,地方性法规为何不能“效仿”呢?
总之,实施性地方法规创设行政处罚,不仅实际需要,而且理论上和法律上可行。当然,这并不是说实施性地方法规可以随心所欲地创设行政处罚。在具体立法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我国行政处罚一度过多过滥的事实,准确把握宪法规定的法治精神以及行政处罚法限制处罚、避免滥罚的立法意旨,谨慎为之。
二、实施性地方法规创设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名称
实施性地方法规创设的行政处罚种类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实施性地方法规只能创设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许可证(执照)等五类行政处罚(以下简称“五类处罚”)。实施性地方法规也没有理由突破此限,设定其他行政处罚种类。
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处罚种类与名称的对应关系问题。一方面,由于立法技术、立法传统以及行政管理本身的复杂性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与具体法律、法规中出现的处罚名称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如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责令停产停业,在具体法规中可能表现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改进、责令改正等;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暂扣许可证(执照),在具体法规中可能表现为暂扣证书、吊扣驾驶证等;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在具体法规中可能表现为没收毒品、没收非法工具(设备)等。这种“一类多名”、“同罚异表”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要把不同的处罚名称误作不同的处罚种类而加以排斥。简言之,实施性地方法规在创设行政处罚时,既不能突破上述“五类处罚”的范围,又要兼顾处罚种类与处罚名称不对应的实际情况。在具体立法活动中,做到依法表述、准确表述、灵活表述,同时要尽量与上位法使用的处罚名称相一致,避免产生歧义。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区分不同类别的行政处罚,避免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尽管行政处罚法仅规定了六种处罚种类,但由于法律、法规可以创设处罚种类,使得实际出现的处罚种类远远超过六种。其中,有些处罚种类易于混淆,可能误以为是“同罚异表”。如通报批评不属于警告,责令限期治理不属于责令停产停业等。这就是说,实施性地方法规在创设行政处罚时,不能望文生义,把不属于“五类处罚”的处罚种类误以为“五类处罚”而加以设定。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