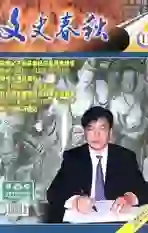陈独秀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
2007-11-22杨飞任玉青
杨 飞 任玉青
1917年1月,在蔡元培校长的力荐下,陈独秀以品学兼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入北大,“一校一刊”实现了历史性会合,再加上北大新派教授的加盟,北大真正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实质上是当时中国思想进步的文化界对于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和认同。因此,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的消息一经发表,立即得到北大进步师生的欢迎和拥护。当时,北大文科预科讲师程演生曾致函陈独秀说:“读报得知足下近掌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必大有改革。”
陈独秀的确没有辜负进步师生的期望,既然执掌了北大文科,他便利用蔡元培赋予他的文科人事和行政权,延聘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学者到北大任教,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壮大了作为新文化运动桥头堡的北京大学的进步阵营。他鼓励和支持文科师生成立各种进步的学术文化团体,出版相应的书刊,使北大新思潮传播得更快、更烈。
陈独秀还致力于北大的文科教学改革。他曾在《新青年》上撰文论述教育方针,指出中国教育的弊端,主张教育应是启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为此,他对北大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科,废除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在文科学生中培养了一批接受新思潮并勇于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优秀青年。
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北大一改往日死气沉沉的局面,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禁区,洗刷了腐朽不堪的校风,一个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新天地出现在北大校园内,科学与民主思潮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
由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同时也由于旧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任何微小的改良和进步,都会引起激烈地反对。陈独秀在北大校园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的结合,以及斗争的进一步深化,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惶恐和仇恨,对新派势力的攻击和压迫也就随之而来。《新青年》对文学革命大力提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清算封建主义旧道德,倡导以“独立自主人格”为核心的新道德,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提倡科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终于使封建士大夫按捺不住,开始了疯狂地反扑。
首先跳出来的是古文学家林纾。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用文言仿聊斋体写的政治小说《荆生》,恶毒诋诬新文化运动。小说中的“三人称莫逆”的田其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那个名为荆生的“伟丈夫”,则是代表旧政治、旧伦理、旧文化的封建卫道士。小说写道:当上述三人聚谈抨击孔子的纲常伦理时,那个随身携有18斤重铜筒的荆生“指三人曰:‘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荆生说罢,还对正欲抗辩的田生“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这些话,把封建卫道士对新文化运动的仇恨心理和盘托出,可谓写得淋漓尽致。很显然,小说的用意在于鼓动北洋军阀政府对陈独秀等人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措施。
同年3月19日至23日,林纾再次在《新申报》发表类似的文字,题为《妖梦》,把对陈独秀的影射之名改为田恒,整篇文字以荒诞的故事表达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对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极端仇恨心理。在这前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的喉舌——北京《公言报》,也直接攻击陈独秀等人。3月18日除了发表林纾的《致蔡鹤卿书》外,还发表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评论,再次攻击陈独秀等人“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诽孔孟”的言论,并说其“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
由于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封建势力便把对新制度的仇恨都倾泄在他的身上。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私德方面确有失检的地方,旧势力便借题发挥,拿他的弱点大肆渲染,利用小报、传单造作谣言,把不堪入目的传闻作为事实,对他进行诽谤,以此达到破坏新文化运动的目的。
还在陈独秀未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前,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就“窃窃私议,啧有烦言”,他们对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鼓吹科学与民主”十分反感,视之为“洪水猛兽”,攻击陈独秀“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的一系列改革,更使得守旧派日益愤恨和不安。由于蔡元培对陈独秀的信任,陈独秀又掌握着北大文科的人事、行政大权,因此守旧派没有轻举妄动。随着陈独秀改革的深入和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守旧派终于对陈独秀开始了疯狂攻击。
辜鸿铭以宣扬“尊王尊孔”大义与新文化运动对抗,他指出“中国优秀的文言文的特点是优雅,非白话文可比”,指责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可笑的,伪善骗人”的。黄侃在其所编《〈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梁漱溟在北大积极宣扬孔子哲学,组织“孔子研究会”,与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北大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慨然于国学沦夷”,出版《国故》月刊,宣扬旧文化、旧道德,反对新文化运动。
更有甚者,北大文科学生张厚载投靠旧势力,从背后向陈独秀施放冷箭。张厚载当时是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兼北京《神州日报》记者,1919年2月间,他两次在《神州日报》撰文造谣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由此已离京赴天津,态度消极。”同年3月初,张氏第三次在《神州日报》发表通讯,又造谣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处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这样的谣言,使蔡元培及陈独秀等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恰在此时,社会上又广泛传出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妓院之地)嫖妓女的流言,更为顽固派的“驱陈运动”火上浇油。由于在私生活方面确有不检点之处,尽管陈独秀曾加入蔡元培于1918年1月发起成立的有“不嫖不赌不娶妾”戒律的进德会,并当选为委员,但仍不免出入八大胡同。这就授人以柄,为北京的御用报纸攻击陈独秀提供了借口。1919年3月,国会议员张元奇以陈独秀的私生活情况向国会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蔡元培。
旧势力对于陈独秀的极端仇恨以及相应的造谣诬蔑,影响了北京大学内一些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也要求遏制陈独秀,如原先向蔡元培竭力推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汤尔和与沈尹默,转而要求蔡元培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而这种要求在客观上与当时反动势力欲革除陈独秀并驱逐出校,进而“整顿”北大的意图相吻合。这些人本来与陈独秀有私谊,并在北京大学内很有地位和发言权,他们态度的变化使得陈独秀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此时,反动的封建军阀政府出场了。正如陈独秀所说的: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想,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1918年陈独秀创办了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更短、与现实联系更直接的刊物《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补充,协同作战,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奋战顽固派。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自然使得反动统治当局怂恿支持那些维护旧道统的士大夫进行反扑。1919年初,旧派人物桐城派古文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拿了几本《新青年》和《新潮》杂志,加以“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批语,面送总统徐世昌,要求干涉北京大学,惩处陈独秀和蔡元培等人。
1919年三四月间,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宴请”傅增湘和蔡元培等人,名为“磋商调和新旧两派冲突之法”,实际上是干涉北京大学,施加压力。3月26日,傅增湘在徐世昌指令下,写信给蔡元培,要求约束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师生。傅增湘在信中矛头直指陈独秀:“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子之幸也”。
在种种力量的压迫下,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及“关系诸君”对陈独秀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事在汤尔和的寓所会商,至“十二时客始散”。会上,主要由汤尔和发言,据他后来回忆,会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当时,沈尹默附和了汤氏的意见,而蔡元培虽然“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因汤氏“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为汤氏的意见所动。这样,那晚的会议事实上已经决定了陈独秀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问题。
关于3月26日晚上的情况,傅斯年后来说:“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此话中的“老谋客”即汤尔和,“还有一个谋客”笔者认为应该是“两个”,即沈尹默和马寅初。
对于如何免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北大采取的是废除文理科,增设教务长的方式。这最初是秦景阳等人的主意,他们不愿陈独秀任“本科”学长,所以秦景阳首先提出废学长,代以教务长。但这个提议蔡元培不乐意采纳,拖了很久,现在因为要辞去陈独秀,又找不到其他好办法,恰好秦景阳调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专门司司长,蔡元培就以废学长为名去掉陈独秀,于是采纳了教务长制度。
4月10日,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陈独秀没有出席,会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首任教务长。至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自然解除。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此时仍为北大教授,并由校方给假1年。事实上,陈独秀从这时起,就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就这样,在封建势力的残酷打击下,在种种反动势力的合力之下,陈独秀被免去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陈独秀思想由此更加“左”倾,为以后与李大钊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在更广的领域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陈独秀被免职后不久,即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更稍后蔡元培也离开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