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消费生命
2007-05-30熊培云
熊培云
毫无疑问,从1992至2007年的15年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整体上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敏感者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卑躬屈膝做了物欲症的奴隶。尽管现在的奴隶与古时候的意义相去甚远,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在物质主义的单行道上,中国人在肉体与精神上仍处于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我消费故我在
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电视里永远关闭不了的是领袖的音容笑貌和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政治宣传,“一九八四式”的“宣传联播”与“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现在,当你走进广州的某家高档写字楼,或者挤上北京的一辆公交车,都会发现,你同样生活在广告屏幕前。过去,客厅作为商家倾倒广告的地方。你可以关闭它,一了百了。但是,今天,你无法关闭电梯口的电视广告。
大众传播与消费主义似乎是一对双胞胎。消费主义时刻煽动人们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这是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幸福转瞬即逝。而广告总是适时甚至超前地给你捎来幸福彼岸的消息,如果你购买它所提供的产品,你便已经身处彼岸之上了。
作为符号世界中的神灵,广告号召每个人赶紧起来自救,要不就赶不上时代,跟不上潮流,被邻居唾弃。唯一的自救方式便是购买商品。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将“免于匮乏的自由”视为人类的四大自由之一。而在广告商那里,世界永远是匮乏的。尽管剥夺人的自由并非商品或者广告的目的,但是在物欲症的逻辑下,所有人都将永无自由。
消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需要”,更是为了“要”,是对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消费因此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它要求人们不只是把消费看作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环节,而是要将其当作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1899年,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美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暴发户群体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凡勃伦认为,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证明,因为荣华富贵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炫耀性消费就是为财富或权力提供证明以获得并保持尊荣的消费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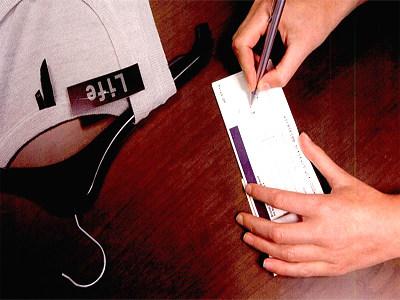
消费心理学研究表明,商品的价格具有很好的排他作用,能够很好地显示出个人收入水平。利用收入优势,通过高价消费这种方式,高层次者常常能够有效地把自己与低层次者分开。在物欲症的逼迫下,人们不断地换房子,不断地抱怨自己家的电视不如墙壁宽,用大屏幕的宽度来见证自己人生的视野与财富的极限。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奢华和高档商品及其形象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符号象征着人们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所以,在奢华消费中,人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已不是商品的实际使用效用,而是炫耀性消费效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变成了“我消费,故我在”。不同的是,和凡勃伦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炫耀性消费已不是那种与大众无关的上流社会的事情,无孔不入的电视已经将大城市里的奢侈风光送到了乡村,构筑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想象。
从公民到房奴
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在《哪儿都不像哪儿的地理现象》一书中,作者康斯特勒说,“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从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个人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每个人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和美国一样,中国的孩子们同样被广告包围,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他们心底被打下某个品牌的烙印,在合适的场合会被购买的欲望引渡。
回顾近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与消费心理的演变,不得不提到90年代末开始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中国老太太说:“我攒够了30年的钱,晚年终于买了一套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临终前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按揭引导人民——正是在这个故事的感召与启发下,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做了“房奴”。与此相关的国际背景是,韩国城市里面积小于59平方米的小型住宅达到40%,日本普通人家的住房面积,大都是六七十平方米,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了省租金,租住两室的公寓,女儿来了就加一个床,一间房睡三个人……
从公民到房奴,一个中内涵同样值得回味。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打拼时,发生在公共领域的事情,自然很少关心。从这方面说,如果公民安心一辈子做“房奴”,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似乎还有些好处,至少它解决了部分“热思想”的“流动性”的问题,不去“惹事生非”。然而,这种平稳的前提是,房奴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不失业。
比尔·麦吉本在《消费的本质》一文中提到自己做过的一个实验:在相同的24小时内录下美国弗吉尼亚州Fair-fax可以收到的100个节目。然后花了一年时间将这2400小时的节目看完,最后发现,在电视构成的世界中,你是世界的中心。确切地说,消费社会的教义是你的欲望是“世界中心。”
就在人们为你这样的无数个“世界中心”而呼吁房价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时,我们同样发现其实房价问题也是个心理问题,否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获得了房屋后还要不停地买房。事实上,他们早出晚归,多半时间并不住在里面,因为他要到外面工作,以便能跟上邻居或同事,换上更大的房。消费主义因此变成了“占有性个人主义”,人们只顾占有多少,全凭个人能力,一切成就仿佛与社会无关。
中国现在是“三代(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同堂”。真正的吊诡还在于中国前现代问题没解决好,先得了一身后现代的病。就像一个男孩,性器官尚未发育成熟,却得了一身花柳病。而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只是为了占有某些物品而不得不贡献一辈子的光阴,物主与物品,究竟谁占有谁?
从教堂到超市
不可否认,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美国人抱怨说,“贪婪已经感染了我们的社会。这是最糟糕的感染。”不过,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关于这一点,相信不少中国人也深有体会。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有人将中国人分为两种:一种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
自然想着有房子,身心焦虑当属正常,奇怪的是有房子的人同样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着更大的房子,如果周围能有片牧场更好。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类的时间。美国人不会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因为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3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人被物奴役,人被物谋杀。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已经是稀有的生活。特里萨修女在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谈到以物欲症为特征的消费主义,《流行性物欲症》一书的作者们进行了很好的剖析。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支柱是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

可以想见,在以经济建设和消费主义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裹挟下,中国人一边脱贫,一边在走向特里萨修女所感慨的那种“贫困”。
如果我们看看高耸入云的教堂以及平地蔓延的大型超市,就知道为什么消费主义在中国势如破竹。中国在80年代初期失落信仰并一步步进入消费社会的时候,心灵生活何其落日飘摇!
如有中国学者分析,西方也好,中东也好,南亚也好,当这些国家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依然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虽然宗教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世俗价值观之间有紧张和冲突,但从西方的历史传统来说,世俗与神圣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二元世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撤。与此相反,与世界上这些国家和地域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世俗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而现在,以举国之力搞经济,同样推动消费主义的“野蛮增长”。与此相关的国际大背景是,“1990年代以后,当中国更加深刻地卷入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和文化生产关系之后,本土性的物欲主义价值观得到了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席卷全国,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种暴发户式的“没有灵魂的物欲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由于中国社会刚从政治禁锢中渐渐走出,当时的消费主义从本质上说伴随着人性的复苏。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欲也渐呈井喷状态,消费观念渐渐向物欲症演变。如果说80年代人们在物质与心灵之间徘徊,那么90年代以后,中国人则走上了一条物质主义的单行道。
梭罗的森林
简单的,是美好的。现代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促进消费主义文化在人群中产生并蔓延。消费能力一度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不过,也有人通过不消费改进生活质量。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有10名美国人结成拒绝消费的“友情同盟”,如今,他们已经坚持了一年不购物的生活。
2005年12月,在美国旧金山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上,10名收入属于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决定尝试一年不消费。他们戏称自己为“签约者”,就像1620年签订《五月花公约》的清教徒决意追求高尚生活、拯救灵魂一样,“签约者”希望在铺天盖地的“大众消费”文化中急流勇退,寻找高品位生活真谛。
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一年间,10位“签约者”只购买生活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卫生纸、内衣、牙刷等,其他物品则通过借、交换、自制和二手易等方式获取,还有些物品则是循环使用。“签约者”在这一年里同样遇到一些问题,但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如果需要添置衣物,他们会去二手服饰店或慈善义卖店。如果孩子需要玩具,他们会领着孩子到玩具店过上一天,尽管最后什么都不买,但孩子们还是很快乐。10位“签约者”的本意并不是为了省钱或保护环境,只是想使生活变得简单而美好。
与此相关的反抗还有杂志编辑考尔·拉森从1992年起就倡导“无购物日”,呼吁人们不要在感恩节后的节日购物狂潮中挥霍;2003年,《今日美国报》专栏作家克雷格·威尔逊表示,他将在一年内只购买食物、卫生纸和赠礼。种种迹象表明,在欧美国家,许多人对消费主义的攻城略地保持着一种警惕甚至反抗的态度。
就像熟读法国《人道报》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造成悲剧一样,任何文化,如果只是进口并放大其一,而不将其他相关的、相抗衡的力量加以引进,悲剧往往在所难免。从过去中国在政治上一边倒学苏联的进口,到今天大张旗鼓地鼓吹美式消费主义,不难发现,中国人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显然,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反对消费主义的传统。早在美国物欲主义刚刚抬头的1845年,即将以《论公民之不服从》和《瓦尔登湖》名垂人类文明史的梭罗悄悄地带上了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住进了自己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在瓦尔登湖畔,这位离群索居的思想者说:“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
90年代以降,中国人陷入了怎样一种困境?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梭罗悖论”:“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大地繁花四起,古木(而不是广告牌)撑起穹隆,人们能够自由地徜徉在那一片“梭罗的森林”?什么时候,不再被广告上温情脉脉的笑容偷走一生的时光——人们只为了需要而工作,做一个幸福的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