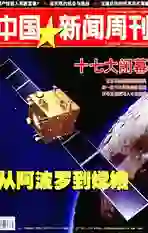反兴奋剂考验北京奥运
2007-05-14万佳欢陈园园
万佳欢 陈园园
两周前,5枚奥运奖牌得主、美国“女飞人”琼斯,在经历7年的兴奋剂纷扰后,终于流泪承认:“我使用了兴奋剂,我欺骗了整个世界。”琼斯禁药丑闻迅速占据了各大媒体头版。为北京奥运而建的反兴奋剂中心即将投入使用。反兴奋剂,将是北京奥运的最难的攻坚之一。
10月18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媒体透露,在原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和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即将投入使用。
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将承担北京2008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工作。
反兴奋剂中心位于北京奥体中心院内,新建的实验大楼,外墙为简单的灰色,新的专业检测设备已摆放到位。
反兴奋剂检查如何进行
兴奋剂检查分为赛前检查和比赛检查(也称赛外检查和赛内检查)。赛前检查将由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北京奥组委三方组成一个工作团队,共同确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挑选受检运动员;比赛检查的运动员方案将按照三方共同签署的检查协议实施。所有的检查工作都将在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观察员和国际单项联合会代表监督下实施。
反兴奋剂中心里,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是检测中心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共20余名工作人员,在运动会或者赛事期间,他们负责检查每个项目的冠军及抽检第2至8名运动员,这称之为赛内检查。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博士生导师曾凡星告诉记者,明年的北京奥运会,整体检查数量将由2000年悉尼奥运的2800例、2004年雅典的3500例增加到前所未有的4500例。“涉及拿牌的项目前几名都要查。”检查例数为历届奥运会中最多的。所有的竞赛场馆及奥运村综合诊所将设立41个兴奋剂检查站。

运动员在比赛结束之后接到兴奋剂检料;取尿样时必须与同性别的检察官一同进入卫生间,然后将尿样分装入未使用过的样品A、B瓶中。如果是女性运动员,须将胸至膝盖的部位裸露,使检察官能观察到你将尿样排到取样杯的整个过程。
不过,实验室工作的“重头戏”还不是这个,在非赛事期间,兴奋剂“检察官”们还必须进行通常被称为“飞行检查”的赛外检查。无任何事先征兆和通知的赛外检查,才是想犯规运动员真正担心的——赛内检查更多是一种威慑的作用,很少查出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赵健向记者举例说,“(像)去年全国总共查了9000多例兴奋剂案例中,其中74%是赛外检查查出的。”
赛外检查的特点是不定期贯穿2008全年。他们一般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到运动员们的面前,抽取的是运动员的尿样和血样,或其中一种——运动员不能拒绝接受检查,否则就会受到处罚。
2004年8月12日,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前一天,希腊最著名的田径选手肯特里斯和队友萨努就因为要逃脱赛前的飞行药检,“故意制造车祸”(国际奥委会事后调查称),受伤住院,最后,两名短跑运动员都不得不退出奥运比赛并面临禁赛的处罚。原定的将由肯特里斯点燃奥运开幕式主火炬,他却成了第一个给东道主抹黑的人。
刘翔也因为“飞检”险些错过雅典奥运比赛。2004年7月初的一个周末,他刚要启程随国家田径队到秦皇岛进行赛前调整,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为找手机他错过了田径队的大巴。国际田联委托的飞行药检官员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让他庆幸不已。按照规定,被抽检的运动员如果两个小时之内没有接受药检,将以“逃检”“罪名”被处以禁赛的极刑。
其实这次阴差阳错的意外,是由于药检官员错过了田管中心发给他们的刘翔行踪报告。根据规定,像刘翔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又处于兴奋剂“重灾区”的田径项目——是反兴奋剂工作的“重点控制目标”。
反兴奋剂检测面临的难题
对尿样的检测,技术难度之大难以想象。打个比方,要查出1毫升尿液中含有的2纳克(1纳克等于十亿分之一克)兴奋剂,相当于在5个标准游泳池(50米×25米)的水量中放人一小勺糖,然后随意抽取一小瓶进行化验。
如果检测结果表明A瓶尿样呈阳性,运动员有提出申请打开B瓶检查、召开听证会甚至上诉的权利。不过,“要求检查B瓶尿样、挑战检查程序和申诉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赵健告诉记者。2005年,孙英杰在十运会上A、B瓶尿检结果均呈阳性,之后也进行了听证会,但仍没能逃脱禁赛的判罚。
但是,挑战A瓶检查结果的成功案例仍然存在。
2006年6月,琼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全美田径锦标赛后,A瓶尿样呈阳性,而B瓶尿样呈阴性。琼斯在最后一刻“逢凶化吉”,那时她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对媒体说:“我是清白的。”
2004年,由于被认为与巴尔科实验室的兴奋剂丑闻有牵连,当时正在接受调查的琼斯不得不放弃雅典奥运会的径赛项目,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琼斯就曾经被控使用违禁药物,之后她多次被卷入禁药风波,但从来没有被确认过药检不合格。
身陷禁药传闻7年,无数次药检,却每每安然度过,琼斯的“幸运”让人有些不解。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博士生导师曾凡星分析说,“有可能是她使用的药物、技术比较先进,而我们的检测总是滞后,技术还没有达到那一步;也有可能是时间差的问题——比如她经过严密测算,只在训练中用适量的药,能力提高了、肌肉力量也增加了,而到了正式比赛时,她的药物已经完全代谢掉了。”
琼斯案因其自首而水落石出。但奥运会上不少关于兴奋剂的谜团恐怕永远无法揭开。
在赵健看来,北京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如果在赛前一段时间,某一种新的检测技术或者方法获得突破,我们能否在最短时间内完全掌握和使用这种方法。
新药物很可能侥幸在检测中“逃脱”,美国著名短跑名将格里菲斯·乔伊娜算得上一个典型的案例。1988年,美国“花蝴蝶”乔伊娜在汉城奥运会上独获得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三枚金牌,在此之前的奧运选拔赛上,她更是奇迹般地创造了10秒47这样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女子百米短跑世界纪录——这个成绩到现在其他女子运动员也可望而不可及,尽管乔伊娜短期内成绩的飞速进步和她男子般的体形让世人心存怀疑,但当时任何检测手法都无法证明她服用了违禁药品。直到10年后,年仅38岁的乔伊娜在家中猝死,虽然其解剖的结果是心脏病突发导致,但是很多人与法国反兴奋剂专家蒙德纳一样,相信“是兴奋剂给她的心血管造成了损害,这就是她死亡的原因。”
东道主的压力
琼斯事件曝光后,巴尔科实验室的创始人孔特在10月8日接受美国媒体釆访时,曾这样为她辩护:“她的金牌不应该被收回,因为和她同场竞技的那些选手也都不干净,她们同样都服用了各种能提高成绩的药品。”
事实上,从竞技体育之始,兴奋剂就相伴而生,从不曾远离。越是大型比赛,越是猖獗。“兴奋剂”更是如附在奥运会身上的“魔咒”,无处不在。
早在古代奥运会时,运动员就尝试饮用各种白兰地或葡萄酒混合饮料,或者服用生物碱与酒精混合而成的饮品,以寻求刺激效果,战胜对手。
103年前圣路易斯奥运会上,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率先冲过终点,随即倒地身亡。赛后的检查表明,他在比赛途中服食了大剂量混合鸡蛋清的士的宁。这是兴奋剂在现代奥运会上的首次亮相。
到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兴奋剂使用已经趋向公开化——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猝死。
除了有违公平原则之外,兴奋剂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对运动员身体的危害。这让国际奥委会下决心,从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起进行兴奋剂检查。
可国际奥委会要想区分出那些能促进运动员健康和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的药物,几乎是不可能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授易剑东曾表示,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从此,一场无休止的“猫鼠”较量开始了。一种药物刚被列进禁药清单,就立刻有新的药物开始施用,反兴奋剂工作陷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怪圈之中。其结果如电脑病毒和杀毒软件中的黑名单,国际反兴奋剂联合会的禁药清单越来越长,不断滋生的新药越来越先进,反兴奋剂检测的难度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