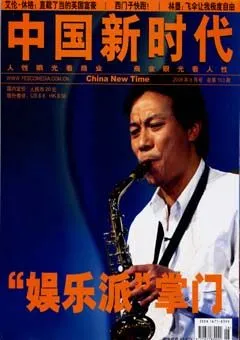王鲁湘:读书,饥肠辘辘后的一场盛宴
2006-12-29权静
中国新时代 2006年8期
刚刚录完节目的王鲁湘,一身黑色丝绸对襟短衫打扮,出现在国家图书馆门口。
生活中的他,倒比在镜头前显得年轻许多,记者开玩笑说,可能是做历史文化类节目的原因,使他在镜头前总有一种沧桑感。
王鲁湘开玩笑的回应,刚刚录节目时穿的那件中式衣服确实有点像“地主老财”。
在凤凰卫视众多精干的主持人当中,王鲁湘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他穿中式衣服,风格儒雅,谈起中华文明来纵横千年、绵延千里。他的文化类节目,不仅在以咨询和评论著称的凤凰卫视独树一帜。在整个通俗文化流行的电视行业,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纵横中国》,讲述中国每个省市的历史沿革、地理特征、风土人情,无不精当;《世纪大讲堂》,把学术的视角带给普通大众,与知识精英一道反思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的若干问题;《文化大观园》,更是凤凰为王鲁湘量身定做的,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无所不包,雅俗共赏。
跟这样一个主持人谈读书,真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好在,王鲁湘对书的感情太深,说起来,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回忆。
抢书与抄书
1978年,一个万物复苏的年份,22岁的王鲁湘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走进了湖南湘潭大学中文系。
自清末出过一个秀才之后,他的家乡就再没出过读书人,于是,王鲁湘一时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子。当时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毛泽东诗词、八个样板戏,他全部倒背如流。
走进大学校门,王鲁湘却傻眼了。有一次同学们聊起莎士比亚.他竟然以为是个女人。王鲁湘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震惊.古今中外历史、文化、文明的知识,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王鲁湘开始了疯狂的阅读。
“一个人,在山里头,已经饿了一个多月了,饥肠辘辘,然后你把他放出来,一桌宴席,你想他是个什么感觉?”王鲁湘这样对《中国新时代》记者说。
从此后,一盏煤油灯,一千多个夜晚,王鲁湘都在读书当中度过。每晚十点半,宿舍熄灯后,他就点上煤油灯接着读。“整个大学阶段,没有在一两点以前睡过觉,每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没有午休,从来没有星期天的概念。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那段时光,是王鲁湘读书的“黄金时代”。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各种书籍都极端匮乏。教材都是老师用蜡质刻在钢板上油印出来的,一抹一手黑,还有浓烈的汽油味。像茹志鹃的《百合花》、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鲁湘最初读这些文学作品,就是这些“蝌蚪文”组成的。
为了买一本书,往往要费很大的周折。有一次,在湘潭大学的布告栏里面,贴了一张新华书店的通知:明天,书店将到一批再版的新书,欢迎读者前来选购。
那天夜里,工鲁湘一直不敢睡,闹钟看了又看,凌晨三点,不等铃。向,他就起床了。穿好衣服走出门去,外面夜色正浓,路上空无一人,也没有路灯,好在月亮还好,给走夜路的王鲁湘带来一些光亮。
大半夜的根本没有车,30里路,王鲁湘是跑着去的。凌晨五点,到了城里的书店一看,自己还是姗姗来迟!
书店门口人头攒动,城里人早已“近水楼台先得月”,排到王鲁湘已是100号了。等轮到他时,书已经所剩无几,他想要莫伯桑、莎士比亚的书,都已经卖空了,只剩下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还有就是李准的小说集和赵朴初的诗集了,虽然不是最想要的,王鲁湘还是买下了。
这几本书王鲁湘一直珍藏到现在,“我还记得李准先生去世之前,我们在一起过春节,当时我还说.要是我今天把这本书带来,把这个故事写上,你再在这上给我签个名字,多有意义啊,纪念那个年代!”
即便是再费心思,还有些书是买不到的。有一次,王鲁湘和几个老同学约好了一起去爬岳麓山,先在山脚下的湖南师大集合,在师大同学的宿舍里,他看到了一本《艺术哲学》,于是,就拿起书翻了两页。
“虽然只翻了两页,但是震撼非常大,当时我就知道,这本书一定要抄,不抄不行!“这本书是同学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没有再版,市面上也根本找不到,而且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还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今天你们去玩吧,我回湘潭去了,这个星期这本书归我,下个星期天我来还给你。我就拿着这本书,买了一张公共汽车票,回到了湘潭.到了湘潭,就开始抄。”
一个人抄不完,王鲁湘就动员了一个跟他一样爱书的女同学一起抄。两人分了一下工,白天女同学,晚上王鲁湘,一个人睡了.就另一个人抄。熬了一周的时间,用完了一瓶多墨水,两人竟然在一周之内把40万字的《艺术哲学》抄完了。到现在,王鲁湘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怎么完成了这项工作。而当年那个和王鲁湘一起抄书的女同学,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太太。
王鲁湘这样抄过的书还很多,毕业的时候.能抄20多万宇的笔记本已经抄满了20多本,整理的卡片有好几箱。
为美学疯狂
大学二年级以后,王鲁湘的兴趣扩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他开始广泛的去听历史、哲学。心理学方面的课。而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整天逃课的他也是异常宽容,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学生肯定不是在玩耍。
渐渐地,王鲁湘迷恋上了哲学,文学方面的书倒越看越少了。“当时就是觉得读小说是一种很奢侈的生命的浪费。在那个时代的气氛之下,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的问题,文学的那些关于人的情感、命运的东西,都变得特别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不在大学这个阶段,对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思想的巨人能够有所了解?当你已经知道泰山的时候,再看古兰山就是一座矮山,更不用说古兰山下面的那些小山了。”
黑格尔的《美学》再版以后,王鲁湘早上八点钟坐进教室开始读第一卷的总序。过了年饭时间,又过了晚饭时间,直到天黑了,教室里亮起了灯,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坐在这里一天没动,头疼无比。翻过书来一看,才读了两页,大脑高速运转,他完全沉浸在哲学思考里了。
之后,王鲁湘陆续啃完了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的书,他被那些思想巨人笼罩整个人类精神原野的控制力所折服。大学毕业后,王鲁湘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
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美学疯狂,那是一个追求精神价值的年代,也是王鲁湘读书的黄金年代。在北大,王鲁湘更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直到现在,王鲁湘还很怀念当年读书的那种感觉。
后来,与凤凰卫视结缘,王鲁湘开始做文化类的电视节目,就再也没有时间像上学的时候那样去精读一本书了。凤凰卫视的节奏很快,往往知道下期节目要做什么的时候,离开拍也就几天时间了,这几天之内,王鲁湘要把跟这期节目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搞清楚。如果做一个省份,就要能够和这个省里的专家对话,像“地方通”一样讲出这个省的特点和故事。做中医,要能和中医院的院长聊中医;做风水,要能和风水家谈风水,还都要谈得像模像样。
令人诧异的是.要了解如此海量的信息,王鲁湘竟然不会上网,也从不使用电脑,因为他对机械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就连手机也是只会接打电话,从来不敢去开发什么新的功能。
但在王鲁湘看来,不会上网并没有对他的工作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电脑搜索出来的东西在他看来都非常的不专业,帮助不大。助手们用电脑做的东西,确实没有王鲁湘自己做的好。
“翻书神功”
这种能力一方面来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积累,另一方面来源于他的“翻书神功”。
王鲁湘读书非常杂,他的家也像一个大书库。那些任何人都看不进去的书,他都看得津津有味。像他喜欢读的“山志”,讲一座山的古往今来,出现过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物,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来过这里,留下一些什么文字和诗,写过什么石刻之类的,都是随手记录的文字,毫无章法,王鲁湘却看的很入迷。
翻书神功则更让人惊叹。在每期节目制作之前,王鲁湘会把跟节目内容相关的书尽可能的找来,几十本书,在桌上堆一堆,然后一本一本的翻,也不一定从头翻,有的从中间开始翻,有的从后面翻。翻完后,哪本书里可能有哪方面的内容,心里大概有个数,就扔到一边了。需要的时候,回想起来,在哪个书里面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再回过头去一翻,果然能找到。而且细节和主要的问题都不会遗漏。这样翻,一上午就能翻七八本书。更神奇的是,很多书王鲁湘从最后开始翻,只看最后一点的两个句子,就能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值不值得看。这些,都是这么多年来酷爱读书练成的。
很多人都说,文化类节目不好做,做浅了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做深了又怕太曲高和寡,老百姓欣赏不了。所以,大陆文化类的节目都不挣钱,办一个垮一个,没垮的也是因为领导力挺,苦苦支撑。然而,王鲁湘做的文化节目却在保持精英姿态的同时,在竞争激烈的凤凰卫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有很不错的广告收入。王鲁湘觉得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自己比较真实。
其实人和人之间绝大多数的话题都是一样的.大学教授和“的哥”之间的区别,也仅仅在于表达方式的不同,而且谁说的精彩,谁就能吸引对方。“有的时候在北京坐出租车,你会发现就同一个话题,的哥的表达方式比你的精彩多了,这个时候你就被他吸引。同样的道理,只要你是平等的,不带偏见,不拿架子的谈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他们也会被你吸引,不会因为你是个大学教授就排斥你说的话。”
王鲁湘很自信,只要让他谈开了,吸引的人一定不仅仅是读书人,连老大妈也能被他吸引。最关键的是,“不要拽那些莫名其妙的概念,不要端架子,说点人话不行吗?”
影响下一代
王鲁湘的这种真性情也直接影响了儿子。
儿子从小到大,王鲁湘说任何话从来都不避讳儿子。儿子在人前人后、家里家外看到的都是一个真实的父亲。儿子小时候是个非常瘦弱的男孩,总被别人欺负。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儿子开始崇拜施瓦辛格,觉得他是个英雄,是真正的男人。所有施瓦辛格的电影儿子都倒背如流,包括施瓦辛格怎么从奥地利到了美国,怎么成功的,都如数家珍。
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最喜爱的人》,儿子在作文里热烈的表达了自己对施瓦辛格的崇拜和对他成长经历的看法,却被老师严厉的批评,说不应该崇拜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崇拜雷锋这样的人,而且批评他为什么没有按照老师规定的开头、中间、结尾三段的方法来写作文。
王鲁湘看了儿子的作文,认为写得非常的好,内容很真挚、文章的风格也很活泼。他就支持儿子做自己喜欢的事。从那以后,儿子开始买专业的书籍和训练需要的各种器械,订阅《健与美》杂志,给自己制定训练的计划,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儿子已经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三、身材非常健美的青年了。
儿子从小读什么书,王鲁湘也从不干预。孩子从北大毕业去英国读心理学,完全是自己的选择,父子之间也很少谈到读书的话题。现在,儿子每次从英国回来都会带回来一些欧洲或者美国的实验性的电影,两个人会一起看碟,看完了会一起从哲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当代社会文明冲突的角度来讨论。王鲁湘发现,对精神深度的要求,对问题挑战性的思考,对思维的逻辑组织方面,父子两人竟是惊人的相似。
“孩子以后肯定比我要强。”王鲁湘自豪的说。
提起以后退休的日子,王鲁湘说自己很期待。现在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阅读,最近一次读的小说,还是十多年前陈忠实的《白鹿原》。至于别的书也都是为了工作需要“翻过”的。以后读书肯定还是会精读,以前感兴趣的课题也会捡起来。
但是,那跟功利就没什么关系了,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兴趣。“那时候我也没有压力了,很轻松,那种状态会超越我做电视的时候,也会超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一种更纯粹的状态,那是我非常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