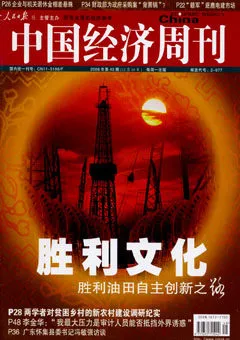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断言太轻率
2006-12-29刘桢
中国经济周刊 2006年49期
从1978年到2004年,全国总人口增加35%;同期就业人口增加87%,城镇就业人口增加178%。
今年6月2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断言:亚太地区的很多开放经济—— 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成功范例——所取得的高速增长却反而致使就业机会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和女性经历了“无就业增长”。
我们认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 “高速增长”是真,而所谓 “低就业”或“无就业增长”则是由于统计口径、手段与方法不适应时代特征而导致的假象或误判。

普查数据不支持“无就业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此过程中,正确的就业与失业数据是难以取得的,因此,即使有这方面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只能是参考,不能据此就对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作出结论。
目前,何为高增长高就业,何为高增长低就业?业界尚无公认的定性或定量标准。但是对于“无就业增长”,则完全可以用城乡人口变动、农业和非农业从业人员变动普查数据的对比,来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判断。
近20多年来,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流动。根据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且长期稳定不变。从1978年起到1996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从82%下降到70%以下,平均每年下降约0.7%;从1996年到2004年,农村人口从70%左右下降到58%,平均每年下降约1.5%。从1996年开始,中国农村人口的绝对数也开始下降,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上述数据是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取得的,应该具有权威性以及很高的可信度。
由于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流动,其基础是农村产生了剩余劳动力以及城镇高速发展缺乏并需要大量低技能、低工资和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因此,这种流动本身就反映了城镇就业机会的大幅度增加。
从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比较,也可以说明中国是高增长与高就业并存。同样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下降到46.9%,年平均下降超过0.9%;同期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29.5%上升到53.1%;在2002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50%;紧接着在200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口首次出现绝对量的下降,从上一年的36870万人下降到36540万人。短短的20多年内,就业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一转变对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用了40余年的时间。
总的来看,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从3624.1亿元增长到136584.3亿元,增长达36.7倍;同期全国总人口从96259万人增加到129988万人,增加35%;就业人口总数从40152万人增加到75200万人,增加87%;城镇就业人口从9514万人增加到26467万人,增加178%。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还没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对增长速度或相对增长速度,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高增长低就业”的断语是轻率的。

统计口径不同导致误差
但“高增长低就业”的看法确是十分普遍,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对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国城镇职工就业弹性系数(指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的计算显示,系数在减小甚至是负数;二是由于城镇下岗失业人群与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汇合,短时期内造成了城镇劳动力供需总量的大矛盾,造成了“就业形势严峻”。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转型阶段,承认就业形势严峻应该是有理有据也是有益的,但是断言“高增长低就业”则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分析或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不能只以“城镇”为视点,而不以“全国”为视点;不能只以“正规就业”的“城镇职工”为基础,而不以符合就业标准的“全国就业人口”为基础;更不能只对“城镇正规就业”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与推理,而不对全国实际就业状况进行观察和分析,否则难免以偏概全。
就以“就业弹性系数”来说,由于对“从业人员”或“就业人员”采用的界定标准不同,统计数据不同,测算出的“就业弹性系数”相差很大。
比如《北京市统计年鉴2004》的全市“从业人口”总数为703.3万人,而《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市“就业人员”为858.6万人,差距高达155.3万人,其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市统计年鉴》未把私营企业雇员和自雇就业者作为“就业者”统计。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完全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测算了不同人群的“就业弹性系数”,详见附表。
从附表可以发现:1990-2000年间,北京市的GDP每增长1%,“从业人口”和“在岗职工人数”出现负增长,呈现出“高增长、低就业”现象;而同期外来从业人口增加0.36%,表明经济增长对带动就业的作用十分明显。2000-2003年期间, GDP每增长1%,“从业人口”增加0.29%,“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基本无增长,而外来从业人员增加约0.69%,这说明进入21世纪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积累下来的就业问题逐步得到消化,社会经济与就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就业弹性系数”呈现出“高增长、高就业”状态。
因此,我们认为,鉴于中国的制度性特点,对中国城镇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并藉以判断经济发展对就业的作用,即使是以统计数据为基础来推测“就业弹性系数”,也应该区分不同的人群进行测算。
就业人数统计数据远低于实际
大量从农村到城镇的就业人员,往往被城镇统计部门界定为“外来从业人员”,既有统计的困难,又有基于习惯势力的忽视。而我们从实际调查中得知,政府统计的城镇就业人数,大大低于实际的就业人数,主要理由如下:
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层层上报统计报表的统计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已无法全面执行。原有统计队伍的人数、统计方法、统计手段等,都没有能力使就业的统计数据真实可靠;我们所接触的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或自雇就业者,几乎不愿意如实地向政府部门申报雇员或帮工人数,大都是尽量少报或不报。这主要是为了少交纳雇员的社会保障费用;三年前北京远郊区在日工资低于18元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露天作业,还有大量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主动上门求职。今年,高于25元/日还无人问津。北京周边农村的青壮年男劳动力都己在非农行业就业,青年女性劳动力也难以在田边地头发现;我们对山西天镇县(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调查发现,该县建筑技工日薪己达70元以上,普通青壮劳动力也在40元/日以上;对山西代县(省级贫困县)一家国营小型制糖厂调查发现,该厂在上世纪90年代下岗的200多名职工,现已全部在当地就业,收入也大为提高。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同意对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判断,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是“高增长、高就业”。此前2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不依靠庞大而廉价劳动力,仅借助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程度;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也远不可能在不增加劳动力总量的前提下,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中国就业形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特点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但转移人口中青年劳动力绝对数量将趋向减少,中年以上和女性人口将相对增多;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定居将大幅度增加;由于取得大城市的户籍很困难,农村劳动力将越来越趋向于在家乡附近城镇就业,大城市所需低技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将越来越严重;全国城镇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将大量短缺,高文化程度的新生劳动力所期望的高薪或管理性职位将长期供不应求,他们可能会感到就业困难,但只要降低或拓展择业目标,就业其实并不会很难。
相关报道
2006年6月2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后,本刊7月10日第26期曾对此作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