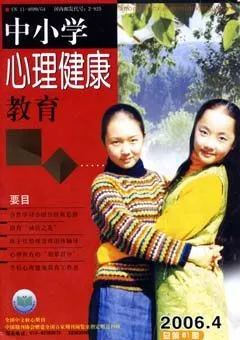1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农民之痛 中国之痛
2006-12-29胡朝阳张振乾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06年4期
面对留守儿童成长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学者警示:他们可能成为被“毁掉的一代”,可能会成为国家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一论断尽管我们难以接受,但绝非危言耸听。
本刊上期刊登了《1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农民之痛 中国之痛》的上半部分,本期请您继续关注。
痛苦、无奈的父母
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据称有上千万。记者曾经采访过来广州打工的年轻的父母。他们对将孩子留在家里的选择只有叹息。如果不出来打工,仅靠微薄的农业收入难以支撑家里的开支,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家庭更是难以为继;出来打工,又对孩子的成长提心吊胆,将孩子带到城里上学,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没有时间看护,也无力承担城市的教育费用。
随州市曾都区某乡镇的某个张姓外出打工者4年回来后,发现儿子已不是以前的“乖孩子”了:离校出走,与校外一帮混混搅在一起,抽烟、酗酒、玩游戏、抢劫、撒谎,染上了许多不良品性。父亲痛苦万分地说:“我真想把我的儿子送进少管所!”
其实,留下孩子外出打工的农民,心中都埋藏着深深的痛苦与无奈……
调查发现,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地方经济不发达,农民靠种田难以维持生计,迫不得已外出打工挣钱造成学龄儿童在家留守的事实。例如,随州市殷店镇东岳庙村,人均1.25亩地(水田),其余为贫瘠的山地,村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香菇和木耳,但由于盲目砍伐山林,又进一步造成了资源的枯竭,从而使相当比例的家庭陷于赤贫。“打工经济”成为养家糊口、解决温饱和走上致富小康之路的主要甚至惟一途径。
调查结果揭示了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个生态周期:外出打工的农民一般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他们的子女这个时候正好处于小学或初中阶段;而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家长外出打工之所以比初中生多,是因为前者的年龄大致处在25~33岁之间(考虑到农村的早婚现象),一般是小家庭刚建立不久,家庭的经济基础较差,可以通过打工来巩固小家庭的经济基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又会逐渐从外出打工转向回乡建设,到了35岁以后,农民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少。
调查人员吃惊地看到了农民外出打工的这个生态周期与其子女的培养形成了一个“悖论”: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原本是为了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使之尽可能地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而教育科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则表明,小学和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子女更需要父母的关爱、指导和家庭早期教育的支持。这个时期父母一方甚至双方的“缺席”,都会在小孩的人格成长上形成某种障碍,影响他们今后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成员。
不少人认为,夫妻一人出外打工、一人留守陪伴孩子,是个好的办法。但实际调查发现,这种办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风险,那就是单亲外出打工容易导致婚姻的破裂。在京山县曹武镇的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单亲外出打工的家庭婚姻破裂的事实。曹武镇朱岭小学校长反映,因为一方外出打工而家庭破裂、离婚的占当地打工家庭的30%~40%。父母的离异又给小孩的身心成长带来阴影。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农村双亲打工的一般要比单亲外出打工的多。这样一来,父母亲的同时“缺席”,又进一步加剧了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父母的作用是至关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远离父母的孩子不可避免地遭遇艰难的生存困境。随州市调查组发现一种“尴尬”的普遍现象,就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子女托给他人监护,实际上是孩子处于“都不管”的境地。因为父母不在当地,造成了孩子的亲情缺失和行为失范,使得学校和监护人在对“留守未成年子女”管教方面处于“二难”的尴尬境地。管松了不起作用,管严了又会导致孩子出走,一旦出现严重后果,无论是学校或监护人都难以承担责任。被调查的几所学校,均提到有打工家庭的孩子出走,弄得学校各方多日四处寻找的情况。在厉山镇高中还出现过一名“留守学生”出走后发生了意外死亡,家长与学校打官司,最后学校赔偿了数万元。因此,学校和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管教,都是备感头疼。
远离孩子的父母们,只有声声叹息。
农民之痛、社会之痛、中国之痛
农民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外出务工,努力改变生活,竟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是农村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个独特的问题,从深层看,它是“三农”问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集中、典型的体现。
我国农民的贫困,根源在于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制度安排,把大部分的福利分配给了城里人。据世界银行对38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研究报告称,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超过2:1的国家十分罕见。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该是5:1,甚至是6:1。中国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世界之最。
在中国8亿农民中,有3.5亿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惟一出路,所谓“民工潮”正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浪潮。顺应历史潮流,进城务工的农民们,不料遭遇了种种困难与尴尬,其中让他们最难以承受的是留守孩子问题。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先生指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它实实在在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如果农民工子女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出现进城的“流动儿童”被社会“边缘化”,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被家庭“边缘化”,那他们离“毁掉的一代”就不远了。
所谓“毁掉的一代”,决不是危言耸听。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后果之严重,犹如冰山下面部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爱与教育,犹如阳光之于幼苗。健全的人格发展,离不开父母爱的呵护。西方有句名言:“一个母亲胜过一百个优秀教师,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在西方,是极少有父母把幼小的孩子托付给别人照管的,这个“别人”包括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怕的是,今天,我国生存着1000万农村留守儿童——1000万个“孤儿”。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留守儿童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孤儿”人格的表现、后果。
“富了一代人,垮了几代人”,人们常用这样的言语提醒、批评那些留下孩子的农民工,这种警示更应该是针对我们的社会、国家。
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同时有1000万儿童离开父母被别人代管,这是绝无仅有的。“农村留守儿童”,以一种令人心碎的方式,体现着“三农”问题。
破解难题,任重道远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组完成调查后,国家教育部陈晓雅副部长用了半天时间,专门听了调查组负责人周宗奎教授的报告,对调查工作充分肯定,表示一定要研究对策,抓好落实,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杨进在2004年11月4日召开的流动儿童工作经验交流会暨研讨会上透露,全国人大正在组织修订义务教育法,教育部已在上报的义务教育法送审稿中,就以流入的政府为主保障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等问题提出了建议。预期,流动儿童教育得到良好解决,势必分流大批农村留守儿童。
教育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规定打工者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应该贯彻两条原则:以接受输入地教育为主,以接受公立教育为主。武汉市教育局执行这一通知精神,2004年对打工者的孩子开放313所一般小学和初中,并批准办了一些民办或半民办性质的学校,如东升学校等等,使打工者的孩子在武汉市有书读。这些孩子参加中考没有障碍,但仍然必须回原籍参加高考。这些措施解决了部分打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同时,武汉市相关部门和学校也承担了一笔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开支。
一位姓刘的家长,其儿子在东升学校六(3)班,一家三口住在20平米的房子里,家住关山。儿子坐校车上学,共收45元,含中午的饭钱。这位家长认为收费很便宜。儿子3年级从仙桃市转到东升学校读书,成绩在班上排前10名。他经常鼓励孩子,对学习抓得严。班主任家访过,提醒家长不能放松孩子的学习。他对东升学校的教学质量满意,希望孩子继续在东升学校读初中。
武汉市的做法,农民工及其孩子比较满意:保证打工者的孩子在武汉市有书读,老师比较负责,政府收费管理到位,学生经济负担不重,这些孩子参加中考也没有障碍。打工者的孩子认为,他们在武汉市学习和生活比在农村好,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学习和生活。调查发现,随州市各地出现了一种“代理家长”的职业。厉山镇每年有近7000名农民外出打工,为给“留守学生”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生活环境,“代理家长”应运而生,据调查人员了解到,这些“代理家长”同留守学生的家长都签订了协议书,家长每年为此要付出1500~1800元的代理费用。“代理家长”除了要照顾好学生的生活起居外,还要负责教育好学生,对其实行跟踪管理,并及时与家长互通信息。据称,厉山镇的“代理家长”数量不少,且这种现象还在向其他乡镇伸延。
京山县坪坝镇唐庙村是全镇有名的打工村,村干部在管教、照料留守儿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全村1312人,814个劳动力几乎在外打工,只有几个村干部和老人、孩子在家里,全村初中生132人,小学生106人。父母在外打工,村干部成了孩子的第二监护人。调查组在唐庙村了解到,村里5名有爱心、负责的干部,每人联系30多个学生,全村的学生都在上学,一个也没有少。
目前,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高度重视并且有所作为的,主要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非常沉重、复杂,破解这一难题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现实中,有力地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教育环境,决非易事。调查中,受调查的教师、校长都认为寄宿制学校有利于“留守学生”的管理、教育,但由于经费原因,许多农村学校无法实行寄宿制,现有的寄宿制学校也由于条件简陋、生活条件太差使得家长不放心孩子寄宿。 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办学条件差,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农村留守儿童很难得到老师更多的关心、照顾。可见,农村留守学生的许多困难,处于农村基础教育整体困难的背景下,真正解决起来,谈何容易。
从根本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人员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打工的农民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给予照顾,原因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种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必须在户籍所在地中考、高考等制度形成的壁垒,农民工无法承担子女入学的高昂费用问题、在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入学无法解决升学考试问题、各地教材的选用不同使得这些群体的子女在转学后面临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等,都成为留守儿童产生的背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状况造成的,是社会转型中的成本和代价,这个成本和代价需要政府、全社会来共同承担,而不应由农民自己来扛。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求解过程,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个曲折复杂、充满艰难险阻的长期过程。时下,中央政府已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国策,而社会公平、稳定,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增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1000万留守农村儿童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完)
(本文作者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编辑/陈 虹 于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