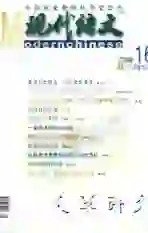“笔以曲而欲达,情以婉而欲深”
2006-09-21史钟锋周爱梅
史钟锋 周爱梅
一、“对写法”之溯源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无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陟岵》
本诗出自《诗经·魏风》,从全篇来看,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行役在外、思家念亲的征人,他登高望乡,想象家中父母和兄长正在惦记他,念叨他,心疼他行役辛苦,希望他保重,盼望他早日平安归来。诗的三章在想象中逐层展现父亲、母亲、兄长想念他、叮咛他的情形,字里行间表露出家人之间那种同命运、共患难,息息相关、心心相连的骨肉深情。在这里,作者不直接写征人自己如何思念家人,而从家人思念自己的角度来写,以实构虚,境界逼真,而且仿佛使人看到了这位征人凝神含情望乡之际那种魂不守舍的形象。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论此诗:“人之行役,登高思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欲达,情以婉而欲深。”
从对面写来,把抒情主体的情思对象化,增强形象性,扩大意境,且由对面生情,从另一方面丰富情感内涵,使抒情更加婉曲蕴藉。这种巧妙的艺术构思,我们称之为“对写法”,其艺术效果借用方玉润先生之言可概括为“笔以曲而欲达,情以婉而欲深”。《诗经·周南·卷耳》也运用了这种“对写法”: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首章写女子采卷耳(一种野菜),采了又采,却连浅浅的筐也采不满,这就暗写她忧思之深,因怀念牵挂远行的丈夫以致心不在焉,无心劳作。后三章则全从对面写来,想象她的丈夫旅途艰辛,人马困乏,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想象他翻山越岭,想象他借酒遣愁,想象他马疲仆病,想象他长吁短叹。她想象得如此真切具体,而这正是她想念、惦记丈夫痛苦心境的反映,虽未著一怀念征人字样,却把思妇的一腔深情间接而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同时让思妇、征人“思怀”的内心感受交融合一,从而达到了“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抒情效果。
《诗经》是我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光辉起点,其细致、隽永的抒情特质,深刻而长远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其中《陟岵》、《卷耳》开创的这种悬想式“对写法”,在诗歌发展的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
二、“对写法”之传承
《古诗十九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可谓承前启后,刘勰推崇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它在诗歌艺术的许多方面汲取了《诗经》的营养,并和诗经一起影响着后代的诗歌创作。我们看下面这首《涉江采芙蓉》中“对写法”的运用。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作以终老!
前四句写女子涉过江去采莲花,江畔芳草萋萋,采了莲花和芳草打算送给谁呢?心上人正远在天涯呢。中间两句自然而然地转换空间,写在女子的遐想中,远在天涯的征人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不见故乡的山水,望不见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展现在他眼前的,无非是漫漫无尽的长路和那阻山隔水的浩浩烟云!最后两句是他们共同的慨叹:相爱的人天各一方,只能让忧伤伴随一生了。“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这两句的“视点”仍是那位采莲女子,表现的依然是她的痛苦思念,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谷《古诗赏析》)的“悬想”式“对写法”,从而营造出“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并且达到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抒情效果。
三、“对写法”之顶峰
在后代诗歌创作中运用“对写法”最充分最巧妙最具代表性的诗作,笔者认为当数杜甫的五律名篇《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
诗人望月思家,却别出心裁地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入微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不说自己望长安月而怀妻,偏说妻子看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懂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诗人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颈联,想象愈加具体化,生动地描摹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句子。香雾打湿了妻子如云的鬓发,清辉静静洒落下来,妻子玉臂寒凉。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望月欲久而忆念欲深,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在诗人心中妻子是那么美丽而多情!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
望月怀远,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一个烂熟的题材,而这首《月夜》却出奇制胜,成为同类题材作品中千古独步的名篇,其魅力无疑来自于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月夜》完全从对面着想,虽只写妻子“独看”鄜州之月“忆长安”,但自己的“独看”长安之月而忆鄜州自然已包含其中,并且把自己对妻子的那份思念和牵挂的深刻——令作者痛入骨髓的不是自己失掉自由、生死未卜的处境,而是妻子对自己处境的担忧——表现出来,而这是一种何等深沉的思念。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论这首诗时曾说:“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真是绝妙的评价!
四、“对写法”之余韵
后代诗词中灵活运用“对写法”的佳作不乏其例,虽是一两句而用之,点滴间仍余韵流香。
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一、二句直接抒写诗人九月九日重阳节对家乡兄弟的深切思念,是一般的写作思路;三、四两句应该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佩带茱萸而自己独在异乡不能参与。如果这样写,虽然也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但却显得平直,缺乏新意与深情。诗人于此用“遥知”翻转一面,化为幻觉,采用“对写法”,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描写家中兄弟对自己的思念之情:他们携手登高,遍插茱萸,本该嬉笑欢乐,却因兄弟两分,天各一方而黯然神伤,把“我思人”的情绪折射为“人思我”的幻觉。这样写,好象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反倒是兄弟们的不得尽然快乐;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不值得诉说,反倒是兄弟们的缺憾更须体贴。这种委婉的手法就巧妙地烘托渲染了诗人的“倍思亲”,把自己对兄弟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更加深沉。
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料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一二句写白居易在驿站中度过全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冬至,夜晚灯前枯坐,形影相吊,显得孤寂凄凉,可接下来诗人并不是直接写自己思念家人之苦,而是遥想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第三句魂飞故里,诗人从家人思己落笔,让对方思念自己的形象呼之欲出,仿佛他们就在自己眼前,由此可见自己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深。这与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出自同一机杼,形象性却更强,笔法显得深透一层。
高适的《除夜作》与白诗相似,都逢佳节,都在馆驿。读完一、二句“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似乎感到诗人要倾吐他此刻的心绪了,可是他却撇开自己从对面写来——“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故乡的亲人在这个除夕夜定是想念着流落千里之外的“我”,想着“我”今夜不知落在何处,想着“我”一个人如何度过今夕……其实,这也正是“千里思故乡”的一种表现。沈德潜说:“作故乡亲友思千里外人,愈有意味。”之所以“愈有意味”,就是诗人巧妙地运用“对写法”,亲人思念诗人,其实恰恰是诗人自己感情的折光,这样写就让深挚的情思抒发得更为婉曲含蓄。
王昌龄的《从军行》(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前三句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正值秋季,又逢黄昏,凉气侵人,边塞征人“独坐”在烽火城西孤零零的戍楼上,寂寥的环境中,羌笛声声,呜呜咽咽的关山月曲调,使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于是水到渠成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那金闺万里愁”。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久戍不归的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偏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得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诗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了。
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上阕描摹暮雨潇潇、霜风凄紧、关河残照、红衰翠减的清秋景色,表达悲秋情怀和羁旅愁思。下阙妙处全在摹拟“对想”,“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一句,就是运用“对写法”,表达自己思归心切的心情。本是作者登高临远,极目天际,却偏想象故园闺中人,应也是登楼望远,伫盼游子归来:她常常在妆楼上痴痴地望着远处的归帆,三番五次地误以为这些船上就载着她的从远方归来的意中人……
(史钟锋,山东科技大学文法系;周爱梅,山东省泰安市第二中学语文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