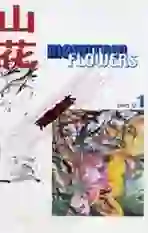赌火车
2005-04-29易清华
易清华
在沦为乞丐的第九天,诗人秋郎和新结识的民间艺人七板,沿着几条荒凉的铁轨朝前走。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农村和城市的结合部,那是一片红壤的11J丘。轨道两边的杂树杂草大肆疯长,好像火车的霞动给了这些植物必要的养分。在眼前一闪,一闪的,是那些在杂草中晚开的映山红。
他们在这条铁路上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了。谁也想不到,他们就靠这条铁路养活着,他们吃乘客们从窗口里扔出来的食物,有时候运气好的话,他们还可以得到半罐青岛啤酒,一大牛截香烟。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奢侈的生活了。
眼前又有一条隧道,他们走过很多像这样的隧道。他们走了进去。每次走进隧道就像走进了自己的家,因为他们没有家。紧贴着青灰色的隧道壁向前行走时,他们就像两只灰色的大蝙蝠。
他们当然没有觉得他们自己就是蝙蝠,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同什么东西比,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的,何况还要同别的东西比。觉得他们是蝙蝠的是一条微瘸着腿的老黄狗。它在隧道里跟踪他们很久了。走近去一看,它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是两个人。
也许是曾经把他们看成了蝙蛹,这条瘸着腿的老狗并不怎么怕他们。它跟在他们的后而走着,后来竟然得寸进尺,用嘴嗅着七板套在一双解放鞋里的脚背。七板一下子火了,一脚就朝那黄狗踹去。
黄狗被踹到了铁轨上,它愤怒地叫了一声,溜走了。
隧道里又恢复了原有的静默。
走出隧道,他们的身边又汇集了两个人,从外表上看,他们比秋郎和七板更惨。衣衫褴褛,体无完肤,肚腹空空,病病歪歪。
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七板神气十足地哼着一曲莲花落。手中的竹板随即响起。
火车来去,白云如画,众鸟翻飞。
七板麻利地扯开了裤裆,掏出了一个灰扑扑的大家伙。七板一耸一耸地在铁轨的枕木上跃动。秋郎看到七板那个大得非同寻常的家伙在他的破裤裆上晃动,跟他嘴里唱的那个莲花落几乎是一个节奏。
七板使劲地吸着他那干燥而且腥臭的朝天大鼻,他带着一种诡秘的神情,紧张地说,兄弟们,这附近藏有一个光屁股女人!
几个人连忙竖起耳朵睁大眼睛,唯有秋郎对七板那种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习气颇为不满。想女人想疯啦,七板,你发什么神经你?秋郎在烈日下对七板大呼小叫。我敢同你赌一条腿,如果在五分钟之内找不到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我就让你砍掉一条腿。七板如此坚定的口吻令秋郎犹豫不决。那另外两个流浪小人见有人打赌,情绪顿时高涨,巴望着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来平衡一下那饥饿、麻木、贫乏、寡味的身心。秋郎考虑到七板不会轻易这么赌,因为一个游走四方的艺人,失去了一条腿,几乎就是要了他的命。秋郎不想赌,不想让那两个靠血腥刺激来调节生活的小人的阴谋得逞。
喂,算你厉害,你是凭什么判断的?秋郎问。
我就凭个鸡巴。
你看你,又不正经了。
老子身无长物,凭的就是这个,跟你开什么玩笑。七板大声囔道。
原来,七板胯下的那个东西,已是一个精怪的物什了。它能够在一公里之内,像雷达对飞机的敏感程度一样,感受到女人的存在。
在秋郎看到的几本武侠小说里,也有类似的事情,不过是讲剑的,说是如果遇到了躲藏在执剑者附近的敌人,这柄剑便呈现血光,且嗡嗡作响,自己从那个超凡脱俗的剑匣里一跃而出,直刺敌人的心脏。
秋郎在想,七板胯下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那样的一把宝剑呢。
果真,在五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几个人也没费多大的劲,就找到了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
女人光滑、白晰的身子隐藏在一篷青草里。她的背后有一棵矮树。油绿的叶子向下翘着,闪着垂涎欲滴的光。矮树的梢上,有一个鸟窠,是这个光着身子的女人用两件内衣盘成的。秋郎几步走近矮树,从那个衣服盘成的鸟窠里掏出一只玩具鸟和一枚圆滑如卵的石子,还有半个干硬的馒头。馒头让秋郎身边的一个小人抢走,另一个则在后面紧追和大骂。秋郎摇摇头,他把玩具鸟和石子捧放在一方枕木上,尔后又去拆那个鸟窠。
就在这个时候,处于昏睡中的女人清醒过来,她嘴里大声嚷着,鸟,谁拿了我的鸟?别动了我的鸟!她把整个赤裸裸的身子倾斜着,疯狂地朝秋郎扑将过来。
女人在狂奔的过程中,逐一展示着她的身子。她的脸上染着层层污秽,但是,在她颈子以下的部分,却一尘不染,雪亮得刺人眼目。宽阔的胸脯上,两个硕大的乳峰大幅度地晃动。两条颀长的大腿莹莹地流光。奔跑中推出了两腿之间的黑影,就像天空深处的鹰,迅疾的飞动和犀利的气势,令人头晕目眩。这是谁家的疯女人呀?秋郎想。
秋郎让这个疯狂的女人吓坏了,赶紧把枕木上那只玩具鸟和石子捧放在由衣服盘成的鸟窠里。我,我给你放进去啦,我不会要你这些玩艺儿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身材高大的民间艺人七板的眼里霎时露出了凶光和欲火。秋郎感受到一头凶猛的野兽从他的身体中脱颖而出。秋郎害怕得闭上眼睛。
那两个抢食馒头的小人已经回来了,虽谈不上饱暖思淫欲,但也算进食了的人眼里冒着绿光,把蓬勃的身子一股脑儿扑向那个没有丝毫防范能力的女人。秋郎见势不好猛扑过去,挡在了那两个小人的前面。两个小人的拳头砸在了秋郎的脸上。秋郎奋力还击。秋郎不堪重负地倒在地上。这时七板一声断喝,那两个小人很快溜之大吉。
七板追上前去。只见七板傲慢地伸出一条腿,把狂奔中的裸体女人重重地绊倒在两条铁路之间的铺满碎石的谷地。
女人就像经过加工的棉花一样,铺在晒得滚烫的石子上,蓬茸松软,吸附着石子上的热气和尘埃。
此时的七板一扫民间艺人的斯文,猛地一把扯掉身上的长裤,整个身子覆盖住女人那棉花一样的肉体。
不要!秋郎惊叫一声,视线与女人那无助的目光交融在一起。
七板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秋郎一眼。秋郎向后退了一步。
秋郎想着怎样搭救这个置身虎口的女人。但是他知道,凭他那一副瘦弱不堪的病体,以及那一套早巳丧失斗志的消极出世的观念,怎么能够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一声吼,又叫他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吼得起来。
但是,那个女人凌乱、散漫、依赖的目光给了秋郎足够的力量。他从她那飘忽的眼神里看到了终极的孤独和火焰。对于秋郎来说,这是他第二次从女人的眼里看到这些(第一次仿佛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是他的初恋。
仿佛绝响。
别!秋郎上前一步。
但是,他很快被正在兴头上的七板飞起一脚踢得老远。
就在这个时候,一列火车呼啸而来。
秋郎在飞速运转的火车前面停住。在火车的对面,在七板肮脏而又强健的身体覆盖之下,有女人的呻吟,以及她那若痴非痴令人为之一振的孤独。然而这一切的一切,皆裹在火车呼啸和震动的强大气流当中。
终于,火车呼啸而去。
沉闷和孤寂照样统治着眼前的世界。秋郎一下子跃过两根铁轨。看见七板以一只屎壳螂的姿势从那个女人的裸体上爬了起来。秋郎一眼看到了七板那种绝望的沮丧。一下子放心不少。
那两个小人又仿佛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似的,在不远处手舞足蹈。他们对七板叫囔着,你中看不中用,中看不中用,还是我来,还是我来。秋郎看见七板胀红了脸,希望他们打起来,那他就有机会营救那个女人。但七板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胯下的那个东西,就像一个蔫萎的黄瓜蒂儿。七板本来斗志昂扬的情绪突然一落千丈。
于是,秋郎彻底放下心来,幸灾乐祸地笑着,毒毒地笑着。
七板用他的大手死命地拉着他胯下的那个东西,他那东西就像蚂蟥一样地拉长拉长,越长便显得越细,看得出上面淡蓝色的筋脉。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七板恐怖。七板焦虑。以往那个见风雄起的家伙哪里去了?
火车火车,你这个缩阳的魔鬼!老子日你的娘!七板绝望地嚎叫,低下头去,用手拼命地擂着那陈旧的枕木和生锈的铁轨,直到上面染着零星的血迹。
那两个小人又消失了,秋郎也收住了笑。
那个鸟窠被拆开了。是两件破烂的内衣,秋郎唱着一首童谣,哄着那个女人,小燕子穿花衣,穿呀么穿花衣。乖乖乖,听话。他用颤抖的手帮那个恍然入梦的女人穿上衣服。把自己一件破旧的外衣给女人披上。女人穿着破旧的男装,在夕阳下显得分外俏丽。
三个人仍然沿着几条荒凉的铁轨朝前走。
七板在杂树林里用露水和一种不知什么香草治了一个晚上,他胯下那个东西终于在第一道霞光的照临下复活了。他又用无比快活的心情唱起了莲花落。
疯女人仿佛被什么所吸引,拔腿跑了开去,她灵巧地绕过三棵竹子、一株松和一个坍塌的石像,找到了一个金色的圆形水塘。这个水塘比一个桌面大不了多少。她想对着这个如镜的水面梳妆。这时,往事仿佛自幽深的塘底袭来,一道如水的光灼痛了她的双眼。
那两个肮脏小人又出现了,像苍蝇一样挥之不去,其中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方绿色的头巾,裹在头上。秋郎朝他们讨厌地挥挥手,他们嗡地一下消失,又哄地一下出现。连七板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几个人匆匆地赶过来,他们看到的景象又与昨天一样。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隐藏在繁茂的草丛中。背后的一棵小树的树梢上,有一个用衣服盘成的鸟窠,因为多了秋郎那件,这个鸟窠就比以前大多了。
两个小人见状,垂涎欲滴,嗷嗷大叫。
七板的裤裆下面如风鼓荡。他又雄起了!同上次一样,七板猛地一把扯掉身上的长裤,舒展身子覆盖住女人那棉花一样的肉体。
不行,七板!秋郎鼓足勇气,用力地扳动七板石磨一样的身体,但是他的身子却纹丝不动。他救不了这个女人,他想离去。他用告别的目光扫了一下在地上挣扎的肉体,又扫了一下旁边那两个跃跃欲试等着分—杯羹的小人。但就是这一瞥,他又从女人那飘忽的眼神中看到了那令他心动的孤独和火焰。
一颗青草在七板的耳朵里、脚心里或者别的什么部位跳动,一种无法抑制的奇痒使他终于不得不放弃身下的女人。他极为沮丧地从女人的裸体上翻了下来。
对性欲的干扰往往来自最轻的事物。一颗青草或者一声汽笛。秋郎深谙此道。
七板一边系好裤子,一边恶狠狠地盯着秋郎。秋郎,这个形影若风的人,吸毒,豪赌,滥交,往日的堕落使他徒具一条人形而已。他靠在一株开着白花的小树上,不堪一击的样子令七板的内心深处感到一阵怜悯。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秋郎眼里喷射出的火焰。七板也不由得一阵颤栗,他知道秋郎不是像苍蝇一样的那两个小人。
其实,我们也可以赌一赌。七板哆嗦了一下身子。以后的路还很长,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了断。
什么方式?秋郎冷冷地问。缓慢会使他的语音变淡,就像一缕烟在风的作用下,悄没声息地淡化在蓝天。
随你的便。七板虚弱的声音在沉闷的空气中穿透。
那两个刚刚消失的人又闻风而来。打赌罗,打赌罗!他们在炽烈的阳光下载歌载舞。
十米之外有一条河。若有若无的流动与周围的阳光和空气融为一个整体。有一只白鸟从河心一掠而起。有一只黑鸟白天空的深处直插河心。几艘高大的轮船来来往往。汽笛声显得很遥远。
站在铁轨上看这河,只能看到一小块河面,就像一张摆满碎银的桌面。
隐隐地有一列火车,从那不可知的遥远和黑暗中驶来。汽笛声如一口热气喷在人脸上,痒痒的。
不远的树林里一片蝉噪。把将黑的天撕开一道道伤口。
火车来了。汽笛声大口大口地吞噬着宁静和孤寂,吞噬着可以吞噬的一切。
秋郎和七板站在轨道上。
火车开过来,开过来,他们站在铁轨上,谁先下去谁就输了。七板要是赢了,他就可以得到那个女人,要是输了,他就要永远离开她。
火车越来越近。秋郎和七板并排站在铁轨上。
这已经不是游戏。这是两个人之间勇气和意志的较量。秋郎看了七板一眼。七板对他不屑一顾。这使秋郎增添了必胜的信心。秋郎出着粗气,火车来临时的震动使他的身体不停地摇晃。
火车离两个人只有十几米远了。钢铁的气息坚不可摧。
延长的汽笛声继续吞噬着可以吞噬的一切。
别玩儿下去了,你下去吧你。你赌不过我的。七板在夜色中对秋郎说。
火车越来越近,五米,四米……七板的脸骤然变白。用颤栗的声音说,别,别玩了,他的身子敏捷地一闪,从铁轨上跳了下去。
秋郎把自己变得傲慢的目光从远方收回。七板的惊惶并没有使他的意志产生丝毫的动摇。他对他不屑一顾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沉静与孤独。火车黝黑而又沉重的影子朝他碾压而来。他知道自己躲不过这一劫了,于是他干脆装出一付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把他的右腿挪到了铁轨的外面,于是他的身子有些倾斜,与迎面而来的火车构成15度锐角。在火车凶猛的态势之下,他挪动右腿的动作显得无比缓慢、无可奈何、心不在焉、可笑之极。
火车呼啸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