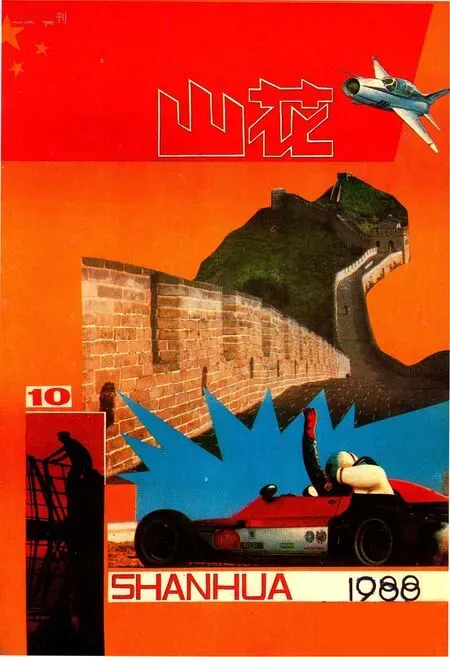积 雪
2005-04-29丁丽英
丁丽英
原来,生殖器的平面特写很奇怪。乍一看,我还以为是一株巨大的毒蕈,拼命吸附在树干上。仔细看,它又像没有生命的无机物:钟乳石,橡塑制品,或陶土的雕塑。反正失去了参照,看着不像跟人体有关。不属于整体的一部分,可也算不上某个独立的物件。说它是幼稚的,贪婪的,生气勃勃的,都可以,但它的表情却是忧郁的,愤怒的,甚至是痛苦的。
老山见我越过他的肩注视着显屏,索兴点出其它的照片给我看,并故作镇定地问:
“怎么样,喜欢吗?”
“无所谓。”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可你们女孩子都在为它疯狂哪!”下了线,老山又狡黠地问,“你不觉得它很壮观?”
“不觉得。”我说,“其实,它看上去倒像似火鸡的脖子。”
“这个比喻好。很生动,可以写进小说的。”
这期写作班的学员,多半来自全国各地,所以都带着笔记本电脑。不过,电脑教室的宽带更好用,又是免费的,进来上网的人也不少。我是来帮门红注册邮箱的。没想到她会找我帮忙。她跟我并不熟,只在开学典礼上见过,好像也没怎么说话,平时更是没机会打招呼。因为我经常逃课,偶尔去一次,也只是坐在后面,而她却像小学生那样,喜欢坐第一排。
“嗨,来了?”门红笑盈盈的,朝我挥了挥手。其实,我一进教室就看见她了。在我和老山说笑时,有两个男生插进来起哄,她却一直缩在角落里没有动,好像连脑袋都懒得抬一抬。
当我走过去告诉她,刚才我们在谈论什么时,门红淡淡地说,其实她早就听见了,只是对这方面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不怎么相信。接着她又说:
“他们男作家真无聊。要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谈论的,就像有些东西不可以写进小说一样。”
我很好奇:“为什么?不是因为害臊吧广
“不是。”她耸了耸肩说,“可能它会破坏审美吧,反正我知道。”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居高临下地望着她。她的个头没我高,是中等偏下的样子,也很瘦。锁骨和平腕处的关节突起着,显得怪可怜的。不过皮肤倒很白,面孔也长得小巧,骨感,是最容易上镜头的那种。眼窝凹进去一圈,眼睛是大了,却白茫茫的一片,不怎么有神。
她按住长长的直发,起身往里挪,给我腾出位置。等我坐下后,她的一只手便很随意地搭到我的肩上。顿时,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水气味。
注册一个新的伊妹儿很容易。我一弄完,门红便喜形于色地说,我帮了她的忙,哪天要请我吃饭。搭在我肩上的那只手也顺势搂紧了我说,不用这么客气的,同学嘛!她沉吟了片刻,说:“其实论年龄,我比你大了许多。”她说得不错,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刚开学那会儿,老山总爱跟我开玩笑,逢人便说,我是他的女儿。我觉得怪无聊的,便制止了他。
那天试好邮箱,我又指导门红到引擎上去搜索。当她看见自己的名下跳出百来条信息时,很是惊讶,便问我,你的名字能搜出几条?我含糊地说,大概几万条吧。后来想了想,又补充说,那是因为我的名字特殊,盛百合,只要和百合花有关的,都会算在我头上。她笑了,鼻子神经质地抽了抽,很怀疑的样子。浏览一番后,她又问我是不是八十年代出生的,我点了点头。她便感叹道:
“怪不得你对网络这么熟。年轻真好呵!张爱玲不是说过,成名要趁早?开学典礼拍集体照那会儿,我就注意你了。那天,你穿了一件透明的吊带超短裙。那种式样的裙子,如今我是不敢再穿了!”
宿舍就在教室和会议室的下面两层。底楼是男生宿舍,女生住二楼。而门红的房间位于楼道口,第一间。从电脑教室下来,她请我进去坐坐。我犹豫着,见她打开锁,也就跟了进去。
单人宿舍都是统一规格,家具的式样,摆放位置,以及墙上的装饰画都一模一样,连床罩和窗帘也是同一种颜色,所以我每次都会产生错觉,以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习惯性地甩掉凉拖鞋,斜倚到床头。我发现自己翘起的脚趾头有些脏。
门红在柜子里翻找,准备送一本她写的书给我。这里的人都喜欢这样,签名送书以示友好。我本想谢绝她,却不好意思开口。我从来没有保存物品的习惯,尤其是书籍,看过就扔,如果上面签了字,扔起来就麻烦了。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好回她的。我的文章都发表在网上。
还好书都送完了,一本也找不到,门红显然有些失望。于是,我让她跟我说说,她那小说到底写了什么。爱情。她说她写的都是爱情,绝望的爱情。还有就是,永远不可能的亲情。
那女孩长得极美,极让人心疼,却没有母亲。母亲在她八岁的时候遗弃了她。女孩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但她血管里流动着的,却是背叛者冷酷而浪漫的血液。所以她的悲剧是与生俱来的,是遗传的。
“果然,女孩继承了母亲风流的天性,大学没毕业就成了未婚妈妈,而孩子的爸爸却始终不能确定。因为她同时和许多男孩谈恋爱,男孩们也对她爱得死去活来。就这样,爱情重复着,生活也在重复。有一天她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早已年华老去,往事不堪回首,现实又无法继续。孤独的痛苦终于擒住她,将她送往等待已久的死神……”
门红没再讲下去,因为吃饭的铃声响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上饭卡,然后跟她一起下了楼。饭厅在对面房子的底层,楼上是图书馆和办公室。写作班的生活很单调,伙食也一样,经常是红烧排骨,咖喱鸡块,白菜豆腐之类,和大学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吃完饭,几个人不是约着出去散步,就是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聊天。自从宿舍的大堂里摆上了乒乓台,就有人在那儿排队打乒乓,看谁先赢十个球。如果下围棋或打升级,则多半是在男生的房间里。据说班委会也重新选举过了。但不管怎样,人们看上去都无所事事的样子,神情也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他们在期待什么呢?写作?交友?更多的机遇?我不清楚。
第二天傍晚,门红在走廊里碰见我,显得很热情。她穿了一套运动服,头发高高地束在后脑勺。她说昨晚本想找我玩的,不料,饭一吃完,我就不见了踪影。她问我躲到哪里去了?我说哪儿也没去,我一直躺在床上看电视,后来很早就睡了。她说多睡觉可不好,这样容易发胖。
“我就比以前胖多了,过去我还要苗条呢。”她说。
我耸了耸肩,没说什么,我不喜欢老是谈论诸如年龄、身材这类话题。接着,门红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女生的瑜伽小组。她告诉我,免费教大家瑜伽的,就是班上的文艺委员王静,她以前学过芭蕾,自己在广东还开了一间健身房。
“那她为什么还要写作?”我问。
“可能想更好地发挥自我价值吧。”她说,“媒体是这样宣传她的——稿纸上的舞蹈者,你从来没听说过吗?”
“没有。”
门红把我带到饭厅,有几个女生已经在那儿了。王静老练地同我打了招呼。她穿着紧身衣,每次向下弯腰时,胃便鼓出来,乳房也不住地颤抖,感觉很滑稽。后来,她坐在软垫上,向我们示范怎样做冥想练习。她说,“这样就能获得内心的宁
静,达到无限的精神之爱。”每天做一到二小时,门红问我能不能坚持?我当然不能坚持了。我说,“就算每天练十分钟,恐怕我也坚持不了。因为这种重复的动作,太单调,看着也很蠢。”
“那是为了控制能量,最终达到快乐的境界。难道你不想试试吗?”王静问。
“不想。”我说,“如果人一直很快乐,不是也很无聊吗?”
这星期,我感觉时间过得快一些了。门红几乎每天都到我的房间来。她对我大学三年级退学的事很好奇,问我是不是因为谈恋爱,还是另有原因。我不愿意说,就把话题叉了开去。还有一次,她跟我说起她的婚姻。离婚后,她一直跟女儿过。但自从女儿去读寄宿学校,她一个人就非常孤独。在这儿,和在家里一样孤独。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也不去打断她。这大概就是她喜欢我的原因?当她说到,现实中的自己并非像小说写的是个未婚妈妈时,注意地看了看我的表情。见我没什么反应,又继续说下去: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一直追求了我四年,所以我一毕业就嫁给他了。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女儿是结婚以后生的。”
“原来,你真有一个女儿啊!”我说。
“要不是有个女儿,我的生活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我问。
“不知道。也许没这么苦吧?但也有可能早就死了。每当再也不想活下去的时候,就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她不能没有我。无论如何,要等她长大了再死。死亡被延期了。一旦死亡可以延期,产生想死的念头,也就变成了习惯。这些年,我经常会想到死。但去死的勇气却越来越小。我也越来越看不起自己了,因为我同样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活下去可能并不需要勇气。”我对她说,“活下去,只是一种习惯而已。”
昨天是星期六,阿伦一大早就来了。在我们交往的这两年多,我也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过他。他坐的是星期五晚上的那趟火车。他说,如果坐飞机,就不可能这么早见到我了。但他在火车上睡不着,一整夜都在想我。那轰隆隆的声音弄得他很烦,以至他觉得火车会一直这样开下去,永远也停不了站,而他也永远够不着我了。我听后似乎有些感动,但他打断我的睡眠,仍让我很恼火。
我们亲热一番后,我接着又睡。阿伦也睡着了。我醒来时,他还没动静。我端详他。他身材修长,结实。喉结、肚脐、阴茎等部位都长得很完美,像艺术品,但似乎跟我都没什么关系。其实,一个人完美的肉体跟他本人的关系也不大。当然,这“本人”指的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坐上出租车,到他预定的宾馆去。学校不准留宿,我更加有理由抱怨它了。阿伦安慰我,像煞心情特别好。我问他愿不愿意到旅游景点走一走?他不想去。他只想呆在房间里看我。我觉得有点无聊,便打开了电视。电视在放沙漠的风光片,我注视着画面中荒凉的景色,而他注视着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搂住我亲吻,用熟悉的手势抚摸我的大腿和乳房,一些敏感部位。他很投人,恨不得将整个身子都钻进来。窗帘没拉上,我感到秋日在我们的身体里流动,即而有一种凉爽的爱意渗透到内心深处。我很满足。
一直到天黑,我们才走出房间,到后海的一家湘菜馆吃饭。我们都很饿,再说,舌头也需要来点新鲜的刺激。吃完饭,我们在岸上散步。天气温和,无风,水波不兴,从游船上传来隐约的丝竹声,像似来到几百年前的秦淮河:颓废,淫糜,还有说不清楚的伤感。这时,阿伦第一次问我:你爱不爱我?我愣了一会儿才回答:总是爱的吧,不过这跟结不结婚没有关系。他又担心我会爱上别人。我说,谁都可能爱上别人的,这世界并不存在永恒的事物。他自言自语道,难道爱情也如此脆弱?我点了点头,但他看不见了。黑暗中,我们谁也看不见水在流动,听不见流水声。我感到自己很麻木。
阿伦是第二天下午走的,我把他送到机场。我们不再讨论共同的未来,似乎眼下的一切就很美好,很清晰,难以忘怀。这种幻觉让我们暂时逃避了现实,彼此沉浸在琐碎的关注之中。“我会想你的。”他说。他把包往上提了提,一边做着打电话的手势。我也朝他挥挥手。可是,当他的背影消失在候机大厅时,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抓住了我——其实他非常陌生,完全是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有一瞬间,我甚至都想不起他的面孔来了。这使我感到恐慌。不过一会儿就好了,又恢复了正
那天晚上,是我主动找的门红。她在房间里穿得很整齐,没开电视,窗帘却拉上了,不知她在里面干什么。
“我在祈祷。”她说,“这样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恩赐,得到爱。”
她为我倒了一杯水,又说:
“不过多数情况下,我更愿意找个人聊聊。你不明白,一个人呆久了,哪怕有个人,光这样坐着不说话,或呆在隔壁的什么地方,弄一点声响出来,也是好的。因为祈祷往往是很难有回音的。”
当她把注意力转到我的身上时,神情就变得开朗了,不那么忧郁,也不那么严肃。
“昨天我看见你的男朋友来了。”她问,“怎么样?你们在一起开心吗?”
“开心。可是最后,不知怎么,我突然觉得他很陌生。怎么说呢?就像从来没在一起过。一切变得很虚幻。”
“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时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十年,按理应该非常熟悉了,可只有到最后分手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嘴巴里竟然有一颗活动的假牙,已经有些年头了。你想,连这种事都不了解,何况其他的呢。怪不得分手后,我们形同路人。”
我笑了,因为我觉得门红的说话方式很好笑。她经常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一下,鼻子仍旧是一抽一抽的。她还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我觉得比较色情——两臂抱在一起,手分别探入另一只手的袖子,上下抚弄着。
门红又告诉我,她是因为前夫的性欲太旺盛,她实在受不了,才提出离婚的。当然,那时她好像也在爱别人。她喜欢亲昵的爱抚,温柔的倾诉;其实,她喜欢的是爱情本身:那种浪漫而神秘的气氛,那种忘乎所以的激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性欲之中。她说这种三毛式的完美的爱情,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但显然没找到。她失望了,不,她绝望了。或许我会幸运一些?我不知道。我说,比起谈情说爱来,我更喜欢直接的方式。
“你跟女人接过吻吗?”她突然问。
“没有。”
“我能吻你一下吗?”
我没有回答,我有点紧张。她挺直腰杆坐着,姿势看上去很危险,臀部只触及椅子的边缘,而小腿悬空交叉着,上身又微微地前倾,为了保持平衡,全身像似在发抖。
“好吧。”我说,“不过快一点。”
于是,门红走过来了。她停下,胸脯正好碰到我的嘴唇。她衣服上的香水气味仍旧很好闻,我把脸贴近去,小心地嗅着,而她顺势抱住我的头。吻过后,我首先笑出了声。我很尴尬,赶紧从她的怀里挣脱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门红没来找我,也没去上课。可能她被自己的举动吓坏了,也有可能在忙别的事情。我不清楚。我安静下来,打算写点什么。但是,不时地,和她接吻的感觉却总要浮上来。那种
感觉,并不如事先想的那么奇特。竟是平淡的,还略微有点苦涩。就像被肮脏的小孩吻了一下,唾液停留在口腔里,因是多余的,特别觉得乏味。可当时,门红看上去却很陶醉。她闭起了眼睛,呼吸还有点急促。后来我们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当我离开时,她突然看了看我,问,“难道你不想知道,我是不是同性恋?”我很想知道,但我懒得问她。
写作班照样是老样子。我也是照样吃饭,睡觉,却什么也没写。时间在流逝,有时会感到焦虑,更多时候,我却觉得这种状态也不错:任事物不停地在眼前发生着,开始或结束,我不去参与,也不去干涉。就像在看一部冗长的电影,除了坐在那儿,你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今天去听了一堂电影课。讲到《法国中尉的女人》,男老师反复播放梅丽尔·斯特林普在堤坝上回眸顾盼的大特写。那海浪之中的惊鸿一瞥,充满了绝望和迷狂,自然地,我想到了门红。我还想象,此刻她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她赤身裸体又是怎样的?
没等下课,老山就发来短信了。他晚上要请出版界的朋友吃饭,想叫我作陪。我不反对,便回了信。编辑是个女的,三十来岁,很干练的样子。和她一起还有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男子,介绍说是京城有名的书商,长得又矮又胖,雪人似的。编辑和书商都很无聊,老山对他们却明显有巴结的意思,碰了几杯酒,就自告奋勇地说起了黄段子:
“一个傻子,在公园里看见一个男人趴在一个女人身上,觉得很兴奋,就问人家,他们在干什么。人家告诉他,他们在做俯卧撑。第二天傻子又来了。同一个地方,真的有个人在做俯卧撑,傻子便走上去模仿。那人很烦,骂道:傻子,走开!傻子回答:你才傻呢!瞧你身下的人都走掉了,你还在这儿一个劲地干!”众人笑了,说我们作家就像那个做俯卧撑的人。
这样气氛活跃了,众人又纷纷说了几段。轮到我,因为懒得讲,便自罚一杯,一口气干了。于是头有点晕,他们后来说了什么,就没听进去。吃完饭,书商面露红色。色迷迷地看着我,提议去泡吧,被我拒绝了。
再次见到门红,是一星期之后。学校组织去香堂摘苹果,快要出发时,她突然从楼里奔出来,跳上了中巴。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长及膝盖的衣摆下,露出湖蓝色的皮裙。她还戴了一顶式样俏皮的鸭舌帽,墨镜架在帽沿上。
“我不怎么喜欢集体活动的。”门红在我身边落座后,抬起脸,注视着我说,“不过,这样就能和你在一起了。我挺想你的。”
我不知如何回答。门红又问,你想不想我?我勉强道,想。不过这两天你在于什么?她告诉我,她在写小说。她在写一个女人爱上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认为这种题材很时髦,但可能不怎么容易发表。门红说,她才不管呢!反正她要写。要不然,心里憋得难受。过分的压抑,会导致精神崩溃。她以前就崩溃过一次。
那时,她刚办完离婚手续,而那个情人却不要她了。这事她以前好像也讲过,却没有这次讲得详细。门红叙述起来,用的是一种嘲讽的语气,有点得意。声音也提高了,似乎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她什么也不在乎。
她是突然对男人失去兴趣的。她说,“你简直想象不出,对一个真实的男人失去兴趣,居然会像脱掉一件大衣这么容易,这么迅速。”
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女孩子的。那些女孩既年轻又漂亮,浑身充满了活力。从她们身上,她重新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青春。
回来途中,门红仍然坐我旁边。一路颠簸,我们都昏昏欲睡,她的脑袋便自然地枕到我的肩上。我动了动,脑袋就滑下去。后半段路,她是趴在我的膝盖上睡过来的。车箱里充满了苹果的清新气味,其中还夹杂着收获者的汗味和门红身上的香水味。隐约中,我似乎还闻到了自己的体香,正从裤缝里渗透出来,扩散到空中,与苹果味、香水味混合在一处。而这混合的气味又将我们团团包围,笼络住,形成看不见的气流,最后,都钻入门红那一张一翕的鼻孔,那里好像无底的深渊。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躁动。后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坛散步,手搀着手,我好像也有类似的感觉。不过,谁又说得清,这一切不是我自己的幻觉?
宿舍里,门红抽着烟,一边将照片像发牌似地摊开在自己的床上。有些是摘苹果时拍的,有些是后来在公园拍的。还有一些,则是学校的背景。照片中,我或站或坐,神情有些冷漠。我俩有几张合影——她总是扶着我的胳膊,侧立着,小鸟依人似地贴住我。也有几张,拍的是风景——宫殿,湖,长廊,几个老头正悠闲地坐在那里吹笛子。
“将来,我可不想这样,吹着笛子,等死。”门红指着照片对我说。
我接过照片。那是在天坛,时间已近黄昏,公园里的游人渐渐少了。我记得那悠扬的笛声,在空荡荡的古建筑上飘荡,竟给人一种美妙得不可思议的印象。
“我倒是满喜欢这种意境的。”我说。
“可这样太漫长了。既没有青春,也没有激情,简直难以忍受!”门红把烟灰弹在保暖杯的盖子上,“其实说心里话,我还是喜欢王朔的那句名言——过把瘾,就死!”
我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她。很奇怪,这段时间她变得很多,几乎像换了一个人。显然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越来越没耐心,也越来越堕落。瑜伽早就不做了,祈祷好像也停止了,最近,她又开始抽烟,抽得很凶。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其它的握紧了,托着腮。这样,她歪着下巴的样子便显得有点无耻,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天真。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晚年拍的一张照片很像。我知道她喜欢杜拉斯,并暗暗地模仿她,可从来没听她公开承认过。反正我无所谓。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每个人都在变,都在重复别人。时间却无情地流逝着。
这会儿已入冬。前两天还下过一场雪,室内的暖气却打得很足,只要穿一件薄绒衫就行了。我走到窗前,把玻璃窗移开一道缝。我看见远处的平房上还留有少量的积雪没有融化,那就像脱了毛的乌鸦,乱七八糟地栖息在一堆,停止了飞翔。而院子里,留在树根上的雪,有的已经变脏。那些没有变脏的,也凝结成小块,或不规则的小球,看上去很像泡沫塑料。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和踩在泡沫塑料上的也差不多。杨树光秃秃的,纹丝未动,完全是一派枯竭的景象。
“那么,你真的要走?”门红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不过她换了一个姿势,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过滤嘴。用力吸的时候,腮帮便会陷下去,鼻根抽搐得更厉害了。整张脸的表情几乎是嫌恶的。
“是。我想回去了。”我说,“阿伦催得太紧,一天几个电话。你知道,上星期他又飞来过一次。再说,这里也没多大意思的。”
门红直接用烟蒂点烟。我提醒她,这已经是第八根了。可她没有理会,继续对我刨根问底:
“那天他来,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说,“他知道我跟你关系好,可能有点吃醋了。另外,他让我……小心你。”
“小心我?是不是害怕我们相爱,甩了他?”
“差不多吧,反正他总是有危机感。你别生
气。”
“我不生气。可是我很想你能够留下来。”
“这恐怕办不到。我厌死了,我要回家。”
“留下吧。再过一个月就挨到毕业了。”
“毕业不毕业,我无所谓!要不是你在,开学一星期我就走了。”
“那么,再为我多留一星期吧。求你了。”
“不,别这样。我最受不了自己依赖一个人了。反正我们会分手。两个女的,你想,这是迟早的事。”
“看来你是对我生厌了。”
“我对所有人都生厌了。”
“你走了,那我怎么办?难道只能去死吗?”
“别开玩笑了。你不会死的。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
“见面又怎么样?反正你抛弃我了。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只有死路—条。而你,也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无所谓。”
那天临走,门红要求再看看我的裸体,她想永远地记住。说着,她捂嘴笑了。很快,她的眼睛就有些潮湿,好像刚被烟熏过,不得不眯细着,眨个不停。
我不忍心拒绝,便同意了。
我背对着她脱了衣服,然后慢慢地转身。我很清楚,我这二十二岁的躯体无懈可击——皮肤光洁,毛发浓密,每个部位都匀称,挺拔,按理说,我应该很自信的。但一想到它有朝一日也会衰老,变得丑陋,被人鄙视,却充满了可耻的欲望,这种自信便陡然消失了。相反,在门红面前裸体,我总是有点心虚,每次都表现得很自卑,几乎是羞愧难当的。
我很快又穿好了衣服。
“再见。”说着,我走向房门。我将手搁在门把上。我等了一会儿,见她没有回答,就开了门。我记得自己一直没有回头。就算回头,我也看不见她了。门已被带上。
确切地说,门红吞安眠药自杀的时间就是那天夜里。可尸体是两天后才发现的。如果她没写遗书,公安局肯定会怀疑到我,因为我的指纹在她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她的身上也有。不过,他们仍然把我叫去做了笔录。对她的死,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想尽快摆脱出来,好回家去。
“听人说,你们俩好像那个,很要好的?”做完笔录,警察又闪烁其词地问。
“是又怎么样?”
“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签了字。警察把我送到门口。他说,死者在遗嘱里给我留了一样东西。但事情没了结之前,他还不能交给我。我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却不肯说。他答应到时邮寄。
收到邮包,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我当场打开了盒子。果然是那只女用按摩器。粉红色的硬塑料,短柄,形棚艮逼真。内置电池。外面套了一只安全套。再外面,是一张家乐福超市的广告纸,可能邮寄时,被人随手拿来包裹用的。
我摸了摸,很凉,几乎没什么感觉,尽管它上面曾经留有门红的体温。我掂了掂,好像也没什么份量。一出邮局,我便连盒一起扔进了垃圾筒。我不放心,又回头瞄了一眼,只见广告纸的一角还翘起着,从垃圾筒里支出来,便退后,将它掖了掖。我确定一切都遮严实了才离开。我迅速地穿过马路,然后拐弯,向阿伦的汽车走去。他已经不耐烦了,在那儿不停地揿着喇叭。
此时,喇叭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惊心,它使我想起那天深夜的电话铃声。可能那是门红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吧。我不清楚。也许我能救她?为此,我自责过,后来也就淡忘了。现在这个世界,谁又救得了谁呢?大三那会儿,要不是我收集的安眠药失效,后来也不可能被人救活的。从此以后,我几乎变成了行尸走肉。这事阿伦不知道。我不想让他知道,一个人没什么理由却想寻死,听上去确实怪吓人的。现在轮到门红了。当然,我也不想把这事说出去。
——之前,大概十二点半左右,门红已经打来过电话,要求到我的房间来,和我一起睡。她说她实在睡不着,性欲难忍,她很痛苦。我没有答应。我说,已经结束了,凡事总有个了结。她不愿意。没多久,我就听见她在敲我的门,在求我。声音低低的,怕吵醒别人。好像她还哭了,可我没有理睬她。我很厌烦。一会儿,敲门声消失了,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又被电话铃声吵醒。我撩起话筒,只听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很沙哑,也很乏力:
“我知道你在里面……”她哽咽道,“我知道你在里面……为什么不开门放我进去?”停了一会儿,她又啜泣道,“人,为什么都会变得这样冷酷?!”
我一直没有说话。后来,我就把电话挂上了。当她再打进来的时候,我没去接。铃声一遍遍地响着,尖厉,刺耳,不停地在耳膜上钻孔,我的心脏开始发痛。但我仍然没有动。
就这样,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之中。我想象自己是一堆正在融化的积雪。后来,铃声便停止了。铃声是突然停止的。跟着降临的,是一片渗人的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