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之爱无根之恨
2005-04-29本刊编辑部
本刊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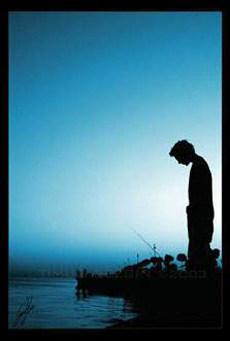
国人眼中的上海,正如新大陆之于欧洲一样,充满了神奇、魔力和诱惑。耀眼的光芒、独特的魅力让许多人蜂拥而至、怡然神往。人们习惯于把那些从别的地方移居到上海,并且有长期居住意向的人称为“新移民”。
相当数量的“新移民”已经成为上海白领、金领阶层的一分子,在激烈的竞争浪潮中努力打拼自己的社会地位。打拼的过程凝聚了他们的悲喜,也包含了他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复杂感情,在此我们将这种感情做一分为二的处理:无根之爱,无根之恨。
又一个“青红"的版本:上海孤儿永无乡
沙然,26岁,记者,来沪2年
三年前的初秋,我打点行装离开了居住十多年的城市,准备回到出生地上海工作。近乡情更怯,心颤抖着,不敢启程。
彼时刚一落脚,走在因为陌生和拥堵而辨不清方向的马路上,像漂泊在汪洋里的一叶扁舟。我忽然恐惧起来,在物质极度繁荣的大卖场和奇高的出租车起步价里强烈感受到生计问题的紧迫与严重。于是,我把一份份简历投向了浦东人才市场。工作人员看了看我的户籍所在地,仿佛有些怀疑似地说:“侬是上海宁?”此话正打在七寸上,我平生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乡关何处,若时间允许,请听我慢慢道来,但是此刻后面还排着一条长龙。一时间我竟语塞了,脸颊莫名地烧起来,支吾着说了一句自己都觉得奇怪的话:“就算是吧……”对方为了体现自己的善解人意,或者为了显示上海人的宽广胸襟,颇为体贴地说道:“欢迎你,新上海人。”

菠萝多一声倒地,天!我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成了“新上海人”?
记忆的微光刹时闪亮起来。此地是我的原乡,第二人民医院里有我的出生记录。然而降临人世仅三个月,我就变成了一朵蒲公英,开始了漂泊的旅程。
记得那年刚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举手报告:“我要撒丝。”老师俯下身听了半天,又看我不得要领地比划着,终于弄明白了,于是大感奇怪:“你怎么不会说话的?”同学中有人撇撇嘴道:“人家是上海人。”突然间,全班同学齐刷刷地看着我。那时的乡下小囡,一年里积攒的心愿也不过是大白兔奶糖、马利水彩笔而已。我自是骄傲,小小年纪,已知在他们眼中,我是不同的另类,上海人的骄傲在血脉里沸腾。
其实,在我回上海定居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全部记忆仍旧停留在童年时代——黄浦江上水雾氤氲,往来不绝的轮渡就像一头头好脾气的蓝鲸;邻家阿婆包的火腿粽子,浓汤赤酱的香味一直绵延到梦里;外婆的橱柜就像魔术师的百宝箱一样能碟碟不休地变出泡菜、烤麸、卤花生和糟凤爪……那时的上海也只不过是个灰头土脸的小丫头,我们曾经多么多么的要好啊!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她一日三变地疯长,摩登得让我不敢相认。更大的难堪来自于,我那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时时刻刻敲打提醒着,在这个我自称为故乡的这个地方,问路简直难以启齿。

于是,我彻底地迷失了,就像我曾经在很多个白天黑夜里彻底迷失在霓虹闪耀的十字街头。上海真真切切的就是我的故乡吗?又或者,她在我的印象中原本就如一痕淡淡的浣花笺上的水印?
这种心情,除非有相似的经历,否则很难感同身受。好友晓萱是某家电台的著名主持人,和我一样也是“支内子女”,所不同的是,她是在大西北的茫茫戈壁里长大的。有时她会带着雨后小鸟般的惊喜跳跃地告诉我说,兰州拉面、刀削面、牛肉面有多么筋斗,白兰瓜、马奶子葡萄有多么香甜。而现在,她回到了出生地武汉,我则回到了上海。有一天她发短信给我:“脚下的这块土地,原本应是自己的故乡,然而我常常彷徨,有种不被收留的感觉。”彩屏里,这句话重回闪烁,我反反复复地看,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又何尝没有不被收留的感觉?零岁,我在上海;三岁,我在北京;六岁,我在河南;七岁,我在湖北;二十三岁,我又回来了。我不停地漂泊,不停地搬家,也许,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仿佛一棵失根的树,长不出让相思鸟停留栖息的繁枝茂叶来。
席慕容,我有多么地羡慕她啊!光是对着穆伦河,对着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这样的名字就神魂激荡,光是听到“青青草地摇啊摇,草原千里闪金光”这样的歌儿就热泪滚滚,可是我,又凭借什么去寄托那无所皈依的乡愁呢?
家乡的英文单词是“HOMETOWN”,而我,是否就是一个只有“HOME”,却永远没有“TOWN”的孤儿?又或者,我就是那个长不大的彼得潘,固守着自己心灵上的“永无乡”?
曾经非常沮丧地对朋友说:“真不知道我究竟是哪里人。”朋友笑笑说:“当然是上海人咯。你出生在这儿,现在不是又回来了吗?”
感谢他的宽容和大度,感谢他的体谅与接纳。也许真如朋友所言,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子,对于这个城市的望闻问切未必如我一样饥渴和细致。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就像是一个从小被母亲交给别人带大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她身边,虽有几许陌生的隔阂,然而我比谁都更加渴望与她骨血相融,与她深情相拥,与她日日夜夜长相厮守……

新移民:一次伤感的错过
小邬,男,25岁,软件工程师,
来沪7年。
记不清楚是在哪一天,我开始注意到地铁站台另一侧的那一个人。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让目光落在她的背影,偷偷地在她乌黑的长发上停留片刻。可是,她不经意地侧过脸的时候,我却急匆匆地收回自己的目光。
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十八岁来上海,读理工科,一直到研究生毕业,在这个城市找一份工作,租房子,独居,周末和朋友打球或者上网聊天,喜欢打游戏,沉默,不曾恋爱。
而她是站台另一侧的那个女孩,穿正装,长发,有淡淡的妆,像个上海女孩。我不知道她每天要去的地方,我只是看她的背影,看她优雅地站在人群中,其他的一无所知。
有很多个早晨是值得怀念的。是一些落在心底的小小的片断,只有一个人会来来回回地翻阅,可是却是无可替代的珍贵。
我买了晨报以后不再站在站台上打开阅读,卷起来放进背包里;我也不关注地铁是不是已经开来,人潮涌动的时候,我开始站在人流的外边。我只是频频地回头,望着另一侧的站台,一直等到那个身影消失,才高高兴兴地挤上地铁去上班。
我曾经在网络上和一个网友说到她,把心底珍藏的那些东西告诉一个从未谋面也不会谋面的人。这是安全的表达方式,我是传统而质朴的青年,不知道如何对着一个人诉说自己内心的激越和感伤。
网友说,或许她也注意到了你,你应该上去向她问好。

可是我一直也没有走过去说一句你好。有好几次,我似乎看到她隐隐地往这一边张望,好像我捕捉到了她的目光,某一个瞬间,我想上去和她打一声招呼,说一句“你好”。可是,她很快地转过头去。地铁站台的另一侧,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一直没有能够走过去,只是目送着她消失在列车带走的人流中。
我的生活即将出现变化的时候,我决定要鼓起勇气给自己一些期许。有一份新的工作,有很好的薪水和晋升的可能,我争取到了,所以我将和原来的生活告别,会坐公司的班车上下班,不会再去地铁站乘坐地铁。
那个早上,我没有买晨报,口袋里有一瓶小小的香水,我想她或许会喜欢这样隐隐的香味。
我站在那里,时光好像停滞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变得异常的漫长。我想她一定会来。
隧道那一头的灯光亮起来,地铁进站。我忽然看到她匆匆忙忙地从楼梯上下来,跑向列车。
我赶紧走过去。Hi,你好。我向她打招呼。
她停了下来,只是四下张望了一下。人太多,她没有看到我。她转身上了地铁,门关上了。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喊第二声,也没有来得及像电影里一样追赶一下列车。地铁呼啸而过。
好像那一段时光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过往,注定有一天会被遗忘。我回到了过去的生活,独居,周末和朋友打球或者上网聊天,有时打游戏,沉默,不曾恋爱。只是我还是会不时想起她站在那里等车的模样,她优雅的身姿和脸上淡淡的笑容。那一些落在心里未曾说出的细微往事有时却让人无限怅惘。

有一些事情却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是一次意外,我偶尔经过那个地铁站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等待中的身影。
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我想这是一个结局,我不应该错过。
我走过去的时候,地铁进站了。门开的时候,她没有动,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从车上下来,拍一拍她的脸蛋。那男孩有着上海男人特有的清爽与细致。
我转过身走上楼梯,听不见自己的心跳。
原来,面对一个上海女孩,我只是走过而已。我在上海没有根,又遑谈爱情。
6年寂寞的流水账
口述:李强,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销售经理,来沪6年。
记录:susufly
1999年12月初的时候,我在武汉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一家上海公司的招聘启事,“大专毕业,工作经验二年”,我看了,很想去上海,但是,中专学历能行吗,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那家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信写得很长很长,都不是关于工作,而是关于我想去上海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信寄出去不久,我的BP机有一个上海的电话,“给你一个来上海面试的机会,如果不行,你就回去。”我想我去了,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
12月29日,我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1000元,离开了武汉,自考才考了2/3的课程,不管那么多了。
12月30日,我到了上海。下火车后,按照上海那家公司提供的地址,坐地铁到了莘庄,面试了,“期望工资想要多少”,“500元就可以了,我可以从操作工做起”,“给你定在800元,500元可能在上海生活很难”“等通知吧,元旦后给你答复”,人事部的人说。

背着行李,站在陌生的上海街头,我第一次感到无助,没有任何熟人的城市,先得找一个地方住。在莘庄镇,很干净,但房子很旧,人来人往的街头,都说着上海话。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房子还没找好,“小兄弟,买袜子吗”,一个湖南口音的小贩,“我想找一地方住”我回答。“找房子?我家有一间空房子,150元……”“120元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在上海的第一天,能这么顺利,居然能在马路上找到一间房子。 1999年冬天,我这样过的。
2000年元旦过后,那家公司打电话给我,说我被录取了。
我开始了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从事手机维修,月薪800元。三个月后,由于工作出色,月薪1200元,半年后,月薪加到2000元。2000年的冬天没有感觉,一直在加班,上海手机刚刚起步,公司效益很好。
到2001年秋天的时候,我终于把自考大专课程全部考完了。这时我把2000元一个月的工作辞了。在上海一年多,第一次积蓄了20000多元。有了这笔钱,我在复旦下面的一个学校读全日制学二年的本科,同时恋上了一个上海女孩。
时间过得很快,2002年树叶黄的时候,我和女朋友已经分手了,由于种种原因,20000元本来计划2年花完,但是,和女朋友的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钱被我花得差不多了,没有钱上学了,也没有女朋友了。
2002年的冬天,我开始了在上海找第二份工作,在松江,蛮冷的天气,蛮远的路程,我去面试,有点不想去,因为是一家台湾公司,后来还是去了,因为有工作总比没有好。
在那家公司,由于工作还比较出色,一个月加班下来,能拿到4000多元,有一次到台湾的机会,只能怪2003年初的SARS,没去成。后来,接着读本科自考,边工作,边考试。
2003年8月,我把一个月4000元的工作辞了,一心一意看书,由于这次自考报了9门,10月底的时候,终于把这9门课考完了。考完试之后,就是找工作,工作一直没着落。2004年5月,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的专场招聘会上我过关闯将,6月终于拿到了OFFER,年薪6万多元,7月开始了我从1999年中专毕业以来的第十一份工作,从1999年的300元到现在的LEVEL。

2005年冬天快到了,自考本科毕业了,没有女朋友,银行里的存款存不到5位数,妈妈恨不得一天打一个电话,要我找对象。
2006年的冬天,不知道还在不在上海,不知道会怎样。 上海这座城市除了钱,还能有什么,如果另一座城市有真爱,我想我不会犹豫去的。就像当年离开武汉一样,义无返顾。
无根之爱还是无根之恨?都有吧。
迷醉着,犹疑着
口述:宗祥谦,台商,40岁,1995年赴上海投资,来沪10年。
记录整理:本刊记者 何菲
我父亲那一代是从上海出去的。我记得小时候,有种说法说上海人是很奸诈的、阴险的,一加一等于三的。我小时候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知道台北市充斥着不少上海人和上海的遗迹,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或者我们刻意把它遗忘。
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或是9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突然又从对面拔起。上海升起来那一刻就像吸星大法,把一切有能力的东西都吸过去了。
1995年我来到上海,住进淮海路上的小洋房,天天经过宋庆龄纪念馆。之后,有人告诉我,这条路就是往昔大名鼎鼎的霞飞路,我的反应有点茫然。一天下午,和朋友路过一间其貌不扬的旧公寓,没有丝毫预警的情况下,忽然,朋友指着那栋建筑物,随口说那是当年张爱玲居住的常德公寓。我一身家常,完全缺少心理准备,扯一下身上邋遢的衬衫,我尴尬地胡乱点头,算是听见了。晚上,搭车回家,走到整装过度新颖的静安寺,对面一栋稍嫌俗气的粉红色大厦,楼下停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们站在车外,三五成群,抽烟聊天。夜很深,街很静,街道显得很空。这里曾是名扬中外的百乐门大舞厅,有人悄悄地在我耳边说。我惊诧不已。

我对上海一无所知。虽然她是我的原乡。
在我还没理解上海之前,我已经去乌鲁木齐路买馒头,去华山路转角上馆子,到吴中路挑选窗帘和沙发布,上衡山路剪发,还在东台路古董市场杀价,为了一只看上去就像是仿造的老钟。我让老板算我便宜些,因为我不是观光客,我是新移民,我只是要摆在自己家里用的。我一本正经地说。五分钟后,我达到我的目的。
即便把这只老洋钟搁在我的电视柜上,我依旧没有意识到我已经住在上海。
我让我的脑子活动着。如一般异乡人该有的反应,想把脑海里所有曾经读过关于上海的书本段落,默默重新温习一遍,我焦躁地想要去书店搜刮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书籍,好好恶补一番。
我其实不懂这个城市。
而我已经进入它的管辖地,成为它的子民。远在我理解上海之前;远在我对上海有任何想像力之前;远在我知道有多少台湾人已经来到这个城市之前。
最后一点使我立刻有了感觉。我看见台湾人在城市街道上开了面包店、泡沫红茶店、洗衣店、照相馆,听见他们在餐厅里高谈阔论台湾政治与计算机软件,一家叫真锅的连锁咖啡店里摆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供人阅览。当走进家乐福时,那些标准台湾话给了我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在台北县的汐止。而无论我去到上海哪里,他们都会告诉我,他们刚刚才做完一个台湾人的生意。书报摊上,标题印得斗大:上海新移民,台湾人。
我们这些台湾来的上海新移民,先是男人只身前来,几年后,便个个在上海置产,举家搬迁。无论衣食住行,他们轻易融入上海市景,无一不惯。甚至很多台湾人因为在上海住得太习惯而觉得不习惯。当初到大陆之前种种臆测,竟然不发生效用。
可是,你发现没有,当台湾人走在路上,无须开口,就能让别人轻易猜测出我们的来历。我们身上有一种气味,肢体有一种语言,脸孔有一种神情,透露我们的台湾背景。我们走到哪里都四处张望,喜好评论,内容不外乎是拿上海跟台湾作番比较。例如,见着了上海的旧建筑,就会提台湾的违章建筑;搭了上海地铁,就要提台北捷运;吃了一道上海菜,就要说台湾也有;看了上海的电视,就谈台湾媒体。

我们越辨认上海的面目,就越花时间描述台湾社会的长相。好像我们不能单独认识上海,除非将两座城市放在一起,我们才能了解上海。我们的根到底在哪里,也是越发模糊了。不过喜欢上海,是肯定的。
其实,住在上海的台湾人与十九世纪在欧洲的美国人有着相似的处境。台湾人一方面在上海处处发现自己自小熟稔、乃至个人向往的文化痕迹,迷醉于这座城市的风华,一方面却又想要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努力要置身事外。台湾人面对上海的犹疑,正因为文化上的轻易跨越,更烘托出政治岐异的进退两难。
所以,一个台湾人来到上海,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大力拥抱这座城市,还是应该保持冷漠的旁观者地位。因为他猜不清他在这座城市的未来。原因是他想不到自己社会的将来。
台湾人其实爱上过无数的境外城市,例如东京、纽约、巴黎……从来也没被人指着鼻子骂过媚俗。每年移居纽约的台湾人数目高过前往上海者,这正好强烈反应了台湾人对上海的说不清的情结。面对上海,台湾人拿捏不准自己的态度,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跟他们的关系,或说,我们还未决定自己该跟对方维持如何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还未琢磨出自己是谁。
众说纷纭:新移民,无根之爱还是无根之恨?
采访:本刊记者(实习) 王威
无根之爱

◆被访者 阿福 外资企业研发人员
来沪时间5年
大学毕业后之所以选择来上海工作主要是觉得在上海这座城市搞IT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的机遇,5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上海这个经济发展迅速且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城市搞IT产业是件很愉快的事。既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又充满了竞争和挑战,激发人的斗志和创新意识,我们搞IT这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环境。这几年来,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公司的肯定,职位也得到了提升,薪水自然也就随之增长了。虽然目前的生活状况和理想中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对将来还是充满了希望的。我眼中的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并没有所谓的“土著”和“移民”之分,谁混得好,谁就是这儿的主人。
◆被访者 Cecilia 保险公司职员
来沪时间2年
有人说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气质类型,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是一个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女孩子,受不了沉闷和呆板的气氛。第一次来到上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动感”城市,爱上了它的包容、繁华和忙碌。也许是因为她的包容,我并没有(像有的人那样)感觉到所谓的“排斥”,相反,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上海的魅力在于她的多元,任何人对于自己来说都是“异己”,同时,又是“同类”。这座城市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每天都在吐故纳新中向前发展。陈旧、刻板与这座城市无缘,每天睁开眼睛都会看到一个新鲜的世界,充满了未知和新鲜。我喜欢这座城市,她对我来说有着孪生姐妹一般的亲切感。
◆被访者 嘉鸣 在校研究生
来沪时间 6年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就读于沪上的同一所高校,5年中上海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为人们提供的机遇以及其重视实践的传统。上海是一座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城市,雄厚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政治环境、频繁的国际交往都为人们创造了发展的机遇,而懂得迎难而上、抓住机遇的人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点上我也深有感触。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我都利用课余时间给自己找一些兼职或锻炼的机会,积累了不少工作方面的经验,而这些工作经验为我现在的就业平添了不少的优势。上海是一座实用性很强或者说是很重视实践的城市,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在这里根本行不通。这里的每个人都很现实、也都很务实,我常常在不经意间为这种精神所感染。
无根之恨
◆被访者 晓飞 外企职员
来沪时间 1年
我是带着无限的憧憬来到上海的。起初也曾经迷恋于这座城市的繁华和精致,可是后来才发现繁华和精致掩盖下的是浮躁和喧嚣。上海是一座物质的城市,不客气地说就是一座“拜金”的城市。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人就像是赚钱的机器,每天不停地运转。看到地铁站里一张张忙碌而面带倦容的脸孔,你会怀疑所谓的“生活节奏快”的解释不过是一种托词。人们常常会在忙忙碌碌中迷失自我,而后又在KTV、迪吧、酒吧等所谓的休闲场所中蹉跎。我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没有归属感,找不到自我价值的生活。
◆被访者 Sissi 文员
来沪时间 3 年
来这里3年了,可我仍要说我不属于这里。上海这座城市很怪,有时胸怀宽广到可以包容一切新鲜离奇的事物,而有时却连一句小小的方言都不能接纳。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在这里会经常遭白眼甚至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上海人的地域观念太强,甚至有些世俗了。户籍制在上海人的观念中可谓是根深蒂固,就像一个很高的门槛把人挡在门外,而能够跳过这道门槛的人,心中也充满了“鲤鱼跳龙门”般的喜悦。3年中曾经谈过一场恋爱,柔情蜜意、海誓山盟败给了地域和户籍,心中仅存的好感和希望也随之消失,剩下的只有厌恶。虽然现在的工作已经逐渐稳定下来,户口的问题也解决了,可我对这座城市仍然充满着强烈的憎恶,因为我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总有一天我要逃离这里。
◆被访者 申钧 房地产公司职员
来沪时间 4 年
很后悔当初选择来上海工作。我出生在农村家庭,在家里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初选择来上海是因为上海的工资水平比较高,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攒下一点钱。4年中我虽然攒下了一些积蓄,可是同日益飙升的房价比起来简直是相去甚远。4年里我总是省吃俭用,极少出去聚会和应酬,更不敢考虑谈女朋友的事,总是觉得以自己目前的经济情况还没有条件考虑这些。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看见身边的同事、朋友出双入对心里面也很不是滋味。曾考虑过跳槽,但是想到自己作为一名本科生在上海找到这份工作也算可以,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恨这可恶的房价,也厌恶上海这座奢华的物质城市。
编辑手记:
入夜,新移民喜欢在那些法国梧桐林荫夹道的老街上散步,享受秋夜的诱人气息。古老依然优雅的小洋房娴静地站在两旁,或隔着一方恬静院子,通过时光隧道,带点好奇但十分节制,不紧不慢地注视着这个城市的新移民们。多少年,多少夜晚,多少个陌生的人,闯入,惊鸿一瞥她生命不同时期的风采,扎下根来或迅速离开。当然,她的外表有些风霜了,可骨头仍硬,穿过树叶的微风也还那么轻柔稳定,仿佛时光不曾流逝,无数平常人的爱欲生死天天在她的鼻下活生生进行着,她早已学会无动于衷。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