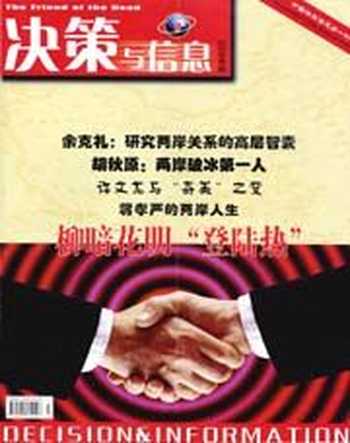中部崛起三问
2005-04-29王晓晖
王晓晖
每天,一条长长的超重运煤车队绵延在大同通往北京的公路上;每天,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都在装船发往武钢、马钢、太钢;每天,安徽金寨县都有农民拿着那张从未见过的补贴明白卡在问:我现在可以取吗?
这些加速着的变化发生在中国的中部,晋、豫、鄂、湘、赣、皖六省,这里人口占全国的近三成,土地占全国的一成多。2002年一个数据的微小变化,使这片古老土地的希望与梦想陡然绷紧。这一年,中国西部地区GDP增长率开始超出中部O.51个百分点,中部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为了全国的尾巴。而中央投向西部4600个亿的建设资金,再加上约5000亿的各类转移和财政补助资金是中部最眼馋的。随后的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之策,更使得中部塌陷之说与洼地之说风生水起。
第一问:中部的优劣何在?
优势劣势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的不同锋面。
这里有中国最好的小麦,也有着全国1/4的贫困县;这里有全国森林覆盖最好的江西、湖南省,也有着全国污染严重城市最多的山西省;这里有长江、黄河,全国水资源量的四分之一,也有全国洪涝顽症的淮河和洞庭湖;这里有中国最多的富余劳力,也有着出外打工最多的人群,到外省市暂住人口占全国的43.6%;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工业体系,也有着沉重的改革负担;这里有全国最密集的铁路、公路和河流,但运出的是煤、粮等初级产品,郑州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的一半是过路车。一句话,中部什么都有,最多的还是发展的空间与潜力。
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列入前五名的没有中部的身影,GDP仅相当于东部的33.6%: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国的15.3%,低于GDP所占比重,说明增长较为粗放;再有两个重要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部六省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除江西外,其余五省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百姓家底仍不殷实。
第二问:中部崛起的结点在哪里?
一个答案:三农。中部2.44亿农民不致富,中国就不会进入小康。面对三农,中部依然两难:不种粮,显然大局上过不去,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小麦第一的河南,油菜第一的湖北,水稻第一的湖南怎能不种地?但只种粮,肯定富不起来。难题可能需要三把钥匙齐来攻破:第一把叫调整结构,农业产业化,粮食深加工,河南凭此由农业大省成为强省。但需警惕不顾条件克隆式、刮风式的一哄而上;第二把叫劳动力转移,但就地转化需要科学规划小城镇,外出打工需要城市的户籍门、社保门公平敞开;第三把是制度钥匙,比如安徽省正低调推进的农村综合改革。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都是为这三把钥匙提供润滑的空间。
第三问:中部崛起的发动机在哪儿?
农业的根本出路是规模化,国际测算只有户均达到30亩地才能实现依靠农业致富,而在中国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工业的发展把人口剥离耕地才能实现。
中部的工业化靠两条腿,一条是迎接梯度转移过来的东部产业,一条是依托自身老本上产业。但细瞧中部六省工业增加值和增值税的变动曲线,便知这里的产业外向度很低,最大的发动机依然是传统的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等高举高打的重化军团,它波及面广,牵动性强,但需要警惕的是资源在时空上的支撑力有多大?去年山西的煤产量是5亿吨,小煤矿挖出了1亿5,消耗了7亿5的资源,而同样的消耗,大煤矿却挖出了3亿5,一个小小开采率的提升可以使资源能够多传一代甚至几代后人。重化工业带来的水、电、土地等资源的高消耗以及污染考验着中部工业发动机的可持续运转。令人欣喜的是中部近几年增速飞快的旅游文化产业和园区经济可能会给六省增加一部更为洁净的引擎。
中部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部的所有问题都带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中国仍任重道远,那么中部发展的帷幕也才刚刚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