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花(短篇小说)
2004-04-29王定国
王定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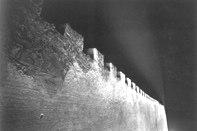
当他背对着晨曦浮上来的时候,鼓满了水气的短夹克仿如漂在水中弓起的猫脊。从他身旁淙淙扑落的急流,在岩块下方冲激出白蒙蒙的水浪,然后沿着潭口的石缝渐次筛慢了流速,平缓地流向卵石滩,流到背着书包的两个原住民小孩的脚前。
“好像是一条死狗。”皮肤较黑的说。
另一个静静凝视着爬满青藻的石岩,漂浮物顺着流向卡在那里,当他捡起石头准备朝它丢掷时,刚刚说话的那个叫了起来:“有头发在动耶。”
两个孩子互看了一眼,同步蹑起脚尖朝上游探试了几步,身背压得极低,仿佛那上面栖着一只水怪。当他们终于辨识出那黑旋的发鬃确定不是水草时,迅即返身朝着水岸上面的产业道路飞奔,背后的书包左右晃浪着,原本流连草泽的水鸟一声接着一声啪啪飞了起来。
1
他曾经使尽全力想要脱身,奈何石洞内好像隐藏着一股涡漩,看不见的力量紧紧吸住他的右腿,以至于当他像个倒栽的稻草人斜插在水中时,额头敲钟般同时打在岩角上。那时月亮缩得很小,只记得挂在岸边的山是黑的,而山的旁边有光,但那种光却又蒙着一层阴灰,很像即将破晓,又似黑夜刚刚来临。总之就是那怪异的光,突然给他带来了临别最后的启示,他已经完了。
现在终于明白了,人怎么去,不就像水一样吗?但究竟昨晚怎么来,怎么会在这里,只是专程一趟散心竟突然掉进这深山,突然落入这冰寒的水底?现在他只不过是个静止的庞然大物罢了,鱼群在他脚底下嬉游,阔嘴郎闪着它漂亮的斑彩,他松脱在皮带外的衣摆下有成群的石宾鱼来来回回翻滚,竟然还有平常罕见、只有在大雨后的浊流中才能偶尔钓获的三角∫怖词酝甲幕魉的肚皮。三角∠褚晃参餐凡嘤写痰男■笥悖然而他却一点痛觉都没有了,就像山边那片阴灰怪异的光所默示他的,他真的已经完了。
一切都来不及交代,时间一到似乎就如同电源的开关突然往下拉断,空气中惟一残余的,是那么天高地远仿如陷入死静之后的空荡荡的回音,那声音很细,很像深秋最后的一缕蝉鸣。求救的讯号已经变成下沉的浮标,现在他能做的,只是把那耳畔仅存的回音连结起来。也许那声音是民宿老板娘阿丽留下来的,是此生所见最后的人,也是此生所听最后的声音。对的,是阿丽没错,昨夜九点过不久,他到树下发动车子,阿丽候在平日揽客的小路口,他把前灯打开,照亮的是她淡红色的睡衣。山村一入夜就特别冷了,何况四处的竹林间刚刚下过一阵雨,她轻揪着胸口的斜襟,倚近车窗大声喊:“不要我带路,那就自己小心啊,路上暗蒙蒙都是石头。”
山溪旁当然到处都是石头,五年来这地带走过多少遍,数已数不清,只是一季没来,芒草已高过山洪冲刷下来的石块,甚至掩没他停在产业道路岔口上的车身。雨后的月亮露脸了,但荒山野地却还是一片黑漆,这样的森冷之地早已汰尽人烟,平常游客大多聚在下游处戏水,顶多几个耐不住手痒的溯溪上来,也只是围在静水的潭面钓钓溪哥或长脚虾,何况不到黄昏便又纷纷收竿归营了。
对他来说这是第一次夜钓。往常来到这山村总是先住一宿,天亮才出发,独自一个在丛林里穿进穿出,哪里是最好的钓点,哪颗爬满青藻的石侧在几时几分之后索饵最凶,他一清二楚。那么,临时起意坚持要来摸黑为了什么,连自己都吓了一跳。九时前一刻,他终于想起来了,那时民宿的门廊提早关了灯,外面只剩青蛙和蚯蚓在黑暗中交鸣,没有其他外客的餐室里摆满一桌他爱吃的山产野菜,但他却突然站了起来。他记得就是这么说的:“我要去钓鱼。”
阿丽并不是从开始就把手护在胸口的睡衣斜襟上,那低开的薄衫随着走动时的摆晃,有时真像晚春初萌的叶芽在风中飘摇;空气中不断有风吹动,一会儿掀出她抖抖闪闪仿佛睨着看人的乳房,一会儿扯开她颈项下的系口,滑出一片雨后初笋刚刚剥壳般的皙白背肌。这样的想像太可怕,没有想到只是和阿丽酌点小酒,微醺后就把自己的思绪弄得如此猖狂,而且那想像还煞不住脚,明明她依然只是侧坐在桌沿,恍惚间他已将她淡红色的睡衣往上脱光,最后只剩一躯绵软的肉身忸忸怩怩横置在眼前。
许多年来早已不曾看过这般淫狎的幻象了,因此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当他突兀地表达“我要去钓鱼”这样的语意时,他竟又同时听见了内心的哭声。他摸黑来到这个熟悉的钓点,原本就是为了让自己赶紧冷静下来,没想到现在却冷静得如同一块冰。幸亏山边慢慢有光,山雀纷纷飞出林子叫醒了他的灵魂,眼看着自己的后背像倾塌的白帆慢慢浮出水面,这一刻他才终于明白,这是命运。
2
松松软软才刚要睡入梦乡,已经有人在外面叫门,在门廊口喊过,便跑到侧院窗边敲着玻璃,不久又绕到后面临溪的灶口大叫:阿丽啊,你有听到莫?
是哪一个烧酒醉抑是神经病,透早天未光就在外面吵弄?她眯开眼,心里咕嚷着,发现还是躺在自己的床上,旁侧也是空的。虽然几年下来一直都是这样,但昨晚那种什么事将要发生的感觉却不断延伸,让她心慌慌,床褥狂抓了一整夜,醒不醒,睡不睡,担心方先生来敲门,敲得小声怕听不见,敲得大声又怕他是把闷酒喝醉了。
阿丽勉强爬起来,淡红色的睡衣上胡乱搭上一件夹克,凑近镜面一瞧,才知道昨晚临时敷上的薄粉还在,像剥开的六月甜桃,摆着放着隔夜不就这般整张脸泛成了铁锈吗?外面的越敲越急,是啥人家火烧厝?顾不得镜里这张脸了,一拉开门缝,村干事阿不拉已经把脸贴上来:“溪仔边死一个人。”
“啥咪人?”只是随口漫应,心里烦斥着,你胡涂找错人了吧。
“他身上没有资料,大家都讲是你店内的人客,警察、法医拢来罗,你赶紧查一下。”
“哪有可能?昨日礼拜三,你想咧,也不是假日,我这里哪可能有人客?”
村干事搔搔头,“这就怪奇,还有谁会跑来这个所在自杀?”
自杀?阿丽蹙起眉,感觉前面路口突然起风了,一大片竹林朝着山谷抖抖索索,顿时一股寒气自她体内浮窜了上来。昨暝不就是在前面路口送他离开吗?她看了村干事一眼,两手捏着夹克领子迅速跑过餐室,绕过三十来坪大的停车场。平常供宿的六间木屋依序筑在成排刺桐树下,方先生每回住的最后一间,门口还开着他喜欢的白白惨惨的马茶花。
车场空地不见他的车,门槛下也看不到他习惯摆着的拖鞋,但她仍然抬起手试探地轻叩,只是嗓音随着刚刚差点跌跤的碎步或者急喘喘的鼻息,早就变成尖扬的怪调,方先生,方先生。有些凄哑的嗓调浮在空中仿佛沾了冰冷的水气。方先生,方先生,她的声音变得浓浊了,张了手掌开始用力拍门,窗玻璃震出了回音。
八年前阿志死的时候也是这般景象,那时娘家阿爸留给她的这片田还没改建民宿,结婚五年就一直住在隔壁村的新洋房。那天也是这样低的气温,不同的是她在屋内,外面拍门的是两个人四只手,震得她捂住耳朵还是吓哭了,“阿丽啊,你头家驶怪手栽落崁仔脚啦!”
她取来备用钥匙递给村干事,自己捂着嘴缩在一旁。窗内木头架上搁着行李袋,他习惯挂在左肩的相机和遮阳帽静静垂在墙中央,空气中闻不出有人待过的气味,推想昨日黄昏他来投宿一直到现在,里面的东西都没动过,床也是空的,枕头和她亲手叠放的被褥齐齐整整搁在角落上。阿丽再也忍不住,凄声叫了起来:“他真正无返来困?!”
村干事似乎松了一口气,“他叫啥咪名?”
忙着掉眼泪,直甩头,两手不停地发抖。对方提来那个行李袋问道:“我打开看好莫?”
“你自己决定啦,不要问我啦。”
她立即退到门外,仿佛那袋子里藏着她害怕的答案。生还是死?喜或者悲?才刚活生生地来,哪有可能一夜就走了?她几乎还听得到昨日黄昏他开车抵达的声音,她从灶房直奔而出,活像自己的丈夫从千年万载的别离中回来了,只差不敢尝试直唤他的名字。方先生!方先生!喜孜孜勾起嘴角轻唤着,她撩起围兜拭着手背,对着挡风玻璃上斜映着的人影和树影;但也只能痴痴傻傻不断地拭着手背八万次,笑得轻轻浅浅,好像内心的愉悦是偷来的。
这种愉悦是慢慢累积的,像她偷偷画在本子里的记号,算得没错便是五年间他来过了十九次,来时总是独自一人,静静地四处走走,静静地扛着钓具下到溪边。说起他的家庭,眼里都是笑意,有个温柔体贴的太太,有个还在美国念书的乖女儿。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谈到自己的生活好像拥有了一切。阿丽听着看着,从羡慕到忌妒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感情是多么难说啊,常常想起民宿刚开张时的景况,餐室里一遇到假日就客满,她忙着炒煮还要兼顾上菜,斗大的汗珠挂满脸,在场子里颠来跑去像个生手。偏偏就常常有人喜欢冲着她盈盈嫩嫩的体态来吃吃豆腐,没有人相信她三十出头就当起寡妇,而且还是个抚养着四岁孩子的母亲。食客中更有手贱的,趁她捧着热汤回不了手,借着闲聊比划顺便摸摸她的屁股。生手做惯了,后来反而泼辣得比谁都厉害,再碰到摸屁股的,她不慌不忙,汤碗平静无波摆上桌,拾起对方缩回去的那只贼手,轻轻拍它两下,这才使劲拖住,硬拉硬扯就是要看着整只手掌浸入汤中。
她不仅学会了一大串粗贱的骂词,杀鸡剁鸭原本畏颤得如同纤手刺绣,如今也俐落得大大出名。感情真的难说呀,半夜里她就禁不住感叹:当她秀里秀气看起来还像个大姑娘时,每天不缺那种狗狗兔兔的客人跟前跟后地追搭,那时她理都不理;等到三五年过去,脸变黑了,胳臂使粗了,反而自己挑上了别人。
挑上了这个方先生啊方先生。村干事抽出行李袋里的文件翻翻看看,好似对着她说话,又像自顾揣测着,“我看拿给他们自己去查吧。”
阿丽还是直摇头,该说好或不好完全都乱了。正像阿志出事的景象,那天她被搀扶到山崖上,看着那熟悉的挖土机如同被肢解的残臂,明明那只失控的钢爪早已晃荡着悬在空中,她还是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中暗自乞求那塞在操控椅下的只是别人。现在呢,一夜没回来,而溪边死了一个自杀的,这时候还能巴望谁当替死鬼———方先生啊,难道你真正甘愿夭寿短命,为什么偏偏要骗我,啥咪婚姻幸福美满?啥咪你有贤妻良母?我看你厝内的查某人(注:女人。下同)是破婊啦,她是讨客兄啦,若不是,我千想万想拢想不出,到底你还有啥理由一定欲走这条短路?
不敢想像这个噩耗要怎么连上昨夜那突然浪漫起来的氛围:像个小女子终于盼到迟归的恋人,她庆幸没有其他外客,可以好好服侍他一个,可以把他爱吃的野菜好好摆上一桌。盼了三个月又三天的阿丽,掌厨的动作充满了节奏,一把锅铲在她汤汤油油孤单寂寞的灶房里挥出了乐章,她同时听见了灶口下方溪谷传来的悠悠水声,那么奇妙,不再是扰人心头。她好像还看得见这一股没头没脑的快乐,虽然只是一个常客,没摸过手,没动过脚,但整个人就是无来由地让她安心。就像晓慧五岁时发着高烧那一夜,幸亏刚巧他来,载着她们母女从小诊所折腾到大医院,他虽然大她十来岁,但抱着晓慧跑起来不管是跨着石头路或者穿行在急诊大厅中那白茫茫的世界,他都像个健步如飞的山中人。就是那一刻,她突然涌起强烈的意愿,希望是自己躺在那个怀抱中快乐地发着高烧,昏昏沉沉,即便睡着也行,死了也没关系,因为生活中其实早就没有其他的依靠可以让她想要活过来。
因而在这难得盼到的夜晚,不想理会外面何时落霜、冬季最后一波寒流到底多强,三十六岁的阿丽反常地换上睡衣,带着不曾有过的羞赧以及她从思念中慢慢储存起来的勇气,佯装无意地来到餐桌,却又显得过度地安静,安静得整个餐室只剩彼此所听见的,对方的呼吸。
她偷偷上过薄妆,坐在他侧面的桌沿,胸前腋下散发着婚前婚后从未开罐的茉莉香水味,淡红色的睡衣让她平素撑持着的悍气瓦解了,虽然不至于衰软得低垂着脸,但是陪他喝点小酒的举措却像个刚刚掀开盖头的娘子,像初生的鸟喙轻轻沾水,像屋后那棵每到黄昏就开始害臊的夜合花。
她帮着夹菜,碗里已有现宰的土鸡肉,何况山芹菜和山猫已经填满了大碗,她夹上的最后一把金针花终于溢出了碗口。也就在这个时候吧,她想起来了,他竟突然站了起来,酒红的面颊对着墙面自语着:“我要去钓鱼。”
想起这一幕,终于不由自主感到羞惭起来,幸亏村干事早已带着资料走远,没多久村里惟一的警车也已经来回走过两趟,奔驰而去的方向正是昨晚他开车离去的地方。还有什么好想的,死就死了吧,只是———为啥咪,明明欲去自杀,偏偏拣我换穿睡衣的时辰,是我的睡衣使你想起人生苦海么?抑是我身躯离离落落使你感觉人生无望么?若人生真正是苦海,也不应该酒菜吃一半,难道莫替我想,我不过是一个查某人(注:女人),好歹嘛是遵守妇道的查某人,听到你忽然间讲“我要去钓鱼”这款推辞的话语,我请问你啦,恐怕你在苦海比我较快乐啦;你莫替我想,我是不是还有面子活落去———想到这里,泪水直扑下来,突然听见屋后溪谷的急流,似乎正以从未有过的湍浪旋起了滚滚回声,像晨起的无边雨雾,将她全身裹住。
3
昨夜摸黑寻找的,不就是现在卡住自己尸体的这块巨石?逆水的石面爬满了青藻,那时手电筒一照,清晰可见硬币大小般的噬痕,那是苦花鱼利用下颔刮食的杰作。他经常采用这种辨识的窍门来寻找藏匿在巨石底下的大型家伙,最佳纪录是二十六厘米长的大苦花,在小瀑布下方一处被激流冲蚀过的深洞里。
刚认识阿丽不久的一次泡茶中,她曾经好奇,为什么特别喜欢苦花这类难钓的高山鱼种?那时他沉默着,但是五年后的现在,不仅不再有机会来跟她解释,也许现在的自己不就像一条被宣告灭绝的苦花鱼硬僵僵地浮出水面了吗?两个学童跑走之后,四周慢慢聚来围观的村农,当他被两名义工抬上岸时,警察立即在他周边系上警戒的黄带,紧接着驱赶的哨子声尖锐地响了起来。
公所来的女职员掩着鼻子,躲在别人的肩后说:“到底是谁呀,为什么半夜跑来钓鱼?”
前面的肩膀说:“你眼睛会不会看?你看那块大石,”那人指着溪中高起的岩磐,“距离溪岸最少六米有吧,何况水潭比较高,不是涉水到潭里自杀,难道他半夜纯粹是钓鱼,不小心落水,然后水往上流,把他冲到那里面?”
插进来的欧巴桑边说边看着警察,“伊讲的真对啦,听讲都市人越来越爱自杀,小小冤家一下就自杀,平均一点钟就有一个,我一个阿婶的亲戚的小叔仔嘛是同款,他———”说到一半,被后面的大手拉走了,“你娘啦,你食饱闲闲是莫?尸体偎近近,讲一牛车不怕他听到?”
他当然都听到了。他惟一想说的是他没有自杀,如果不是嘴巴塞满泥沙,相信凭他满腹的冤屈应该还能挺出勇气把真相说出来。当时虽然喝了酒,但那一点点醉意根本不算什么,否则怎么一到溪边还记得套上钓鱼专用的短夹克?夹克里里外外总共十六个小口袋,用来装置铅珠、子母线、小剪、日本伊势尼鱼钩和转环之类的线器,不到十分钟他已经把两支十八尺长的钓竿分别系好了钓饵。为了避免长夜漫漫地空等待,他在其中一支的竿尖系上点燃的香,接着将竿尾插在脚边的石堆里;另一支则采取直感钓法,直接握在手上,任凭八钱重的铅珠垂到水底,然后抬手绷直母线,等待吃饵的讯息传到手中。
刚开始时他做得多好!就是因为这样的熟稔,学会钓鱼之后的第三年他就轻易钓到了那条大苦花。然而,两支钓竿落水就绪后,这才感觉身体内外突然颤抖了起来。天空只是几点寒星伴着湿濡的缺月,落映在看不见的激流中只剩鳞片般飘忽的折光;而对岸的山是那么黑,黑得太过突显以至于看起来像只魔掌对准了他的脸庞。大约就是这样的缘故才让自己隐隐颤抖起来的吗?起初以为是另一支竿尖上焰红的香点在颤动,是苦花瞬间就饵的强烈讯号。为了换个角度瞧,他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但那讯号很快就消失了。
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似乎就在真正陷入黑暗的瞬间,才发现原来整个世界只剩他自己。那焰红的香点因为风的吹拂,一层层落下它的余烬,好像只剩越来越衰弱的呼吸在风中抗拒着。这时他才发觉根本不该来,不该来做这莫名其妙的夜钓,或许更不应该来这一趟匆匆忙忙的旅程。多么希望还能回到今天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那时女儿还没离开,餐厅人多,他提高声调央求着:“你就让我当个主婚人吧!”
如果可以重来,他愿意再恳求一次,时间不急,她回台北的火车班次随时都有。然而她还是借故要走,回台湾的假期只有五天,有很多杂事要处理,要陪男方家长去挑些东西,还要亲自跑法院把公证时间敲出来,还要……他只好赶紧看着她的脸,三年音讯全无就回来这一次,酷似爱贞的这张脸似乎很快又要消失了。为什么偏要挑麦当劳这么吱吱喳喳的地方相聚?他现在明白了,她是为了要分开,借着人多嘴杂,车声加上杯盘声,可以把话说得很快,不需任何表情或感情,而且把话说尽只需三两句,然后把原本隐藏在心里的继续隐藏起来。
“就这样了。”她说,两手一摊准备站起来。
“我应该出个面,要不以后在路上碰到自己的女婿还认不出来。”
她转脸看看窗外,然后对着玻璃说:“出国念书的时候我答应过你,结婚一定会让你知道,现在我已经遵守了诺言。”
“我也记得。”他垂下脸,看着自己的鞋尖。厂长任内办完优退后再也没有穿过这么光鲜的鞋子了。鞋面黑得发亮,见面之前特地亲手打造,第一层拭净尘埃,第二层敷上油膏,待它自然风干,接着拈住沾水的棉花反复推摩。完工之后重新再来,第一层直接敷上油膏,待它自然风干,同样拈住沾水的棉花,像不断地推摩许多年来生命中不断积累的尘埃,一遍又一遍擦拭,相信总有一天终于可以把心里的苦痛擦光。
是鞋面亮得使人恍惚吗?他突然接不出下文,但时间那么紧迫,她那紧挽着皮包的样态看得出来随时会走,那么———其实他到法院还是查得出哪一天甚至几点几分的公证时间,只是不能明说,以她从刚刚见面到现在一再牵制出来的距离,已经摆明父女两人今后只会更糟;她终于找到一对翅膀,他则注定要在往后的岁月单独看着自己的毛发慢慢掉光。
当他还在思索着如何表达语重心长的一句什么,她已经站了起来,“那我走了。”她说。
这才发现她已长得比自己还高,也蓄了长发,挑染的细丝映现了窗外透进来的光。他不得不跟着站了起来。
想到这一走绝对是更远更久,真想赶紧拉住她,就像拉住许多年前她的母亲一样。但她走得极快,刻意不回头,明明听见他跟上来的脚步声……往火车站的方向,人来人往的骑楼,走了几步之后她终于停了下来,冷冷地问道:“你要做什么?”
他本来要说,我开车送你去车站,但他吓了一跳,她的声音仿若从冲蚀千万年的深洞中回旋出来,那么冷冽空荡。她猝然停脚转身,两人差点撞在一起,那张脸逼近放大,近得看似熟稔,其实非常陌生,陌生到很像他最后的世界中所剩下的最后一堵墙。因而在那大庭广众的墙角阴影下,他只好随意指指骑楼外停得满满的车海,晃晃手中的钥匙,然后低着头说:“没做什么,我去山上走走,去钓鱼。”
计划中并没有上山度假的打算,何况过了周休二日,星期一很可能就是她公证结婚的喜日。但他已经发动了车子,只好开始发呆,车子走走停停,前进后退突然窒碍得如同多年生涯一直在脑海中停格纠结。
车子直行,朝着她的方向。当他看见了喷水池,已经接近火车站尖塔的大钟下。突然瞅见她站在行李库房的尾端面对着墙,虽然只能隐约看见她的背影,但从她曲起的手肘明显可见她正捂住脸低泣着,两个肩头不停抽动,似乎连她的长发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想要返回今天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为的便是抢救这一刻,漫长的生命中也许只有几个重要的瞬间,何况这是最后一个了。他相信爱贞曾经也是站在深夜的许多看不见的地方吧,也是这样捂住脸低泣着。母女两个都有酷似的神韵,从背后看,那颤抖着的千丝万缕仿如弥天大雾,直到现在依然笼罩全身。如果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瞬间都能抢救,那么谁不愿意跑回爱情中直到天荒地老?他绝对愿意切断和一个女人偷偷赁居的那三个月,切断那光溜溜的瞬间。那致命的一幕将永不开启,女的可以把床下的衣裤穿回去,他也来得及把所有的狼狈带走。那么爱贞呢?他想,突然出现在门口的爱贞将也不会哭泣着抖动从那之后再也不曾见过的肩头,她不必惊惶颤泣,不必一直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到永远的黑暗中。
然而最后他还是把车绕出了圆环。为什么自己的人生只剩钓鱼这条路?黑暗中他一只手悬空握住钓竿,另一只手伸入夹克藏在胸口。穿过水面袭来的冷风紧紧将他抱住,不断在一片死静中呼号。
4
最后赶来的检察官,穿过人围走近死者的脚前。“家属呢?”他朝旁边的警察问道。
“还在联络,长官。已经找了很久,恐怕死者最近搬过家,身份证上面的资料还是旧的。”
检察官朝产业道路岔口下方一块高起的土丘指指。“找不到家属,那站在上面哭的是谁?哭得那么伤心。”
“那是附近一家民宿的老板娘。”腋下夹着一卷雪白布幅的村长走了过来,“死者是她的常客,可能已经变成老朋友了吧。”
“请她过来问问!”检察官说。
阿丽啊,阿丽啊!旁边几个多事的齐声喊了起来。阿丽发现突然那么多人同时转头朝她瞧来,嘤泣着的声音立即在喉头嘎住,只剩自己听得见残留在内心的呐喊。她已经在土丘上等了许久。这里是下到溪边惟一的路口,他那婚姻幸福美满的太太要是会来,不就早该露脸了吗?这时她失望地走下土丘,反而在众人的注视下爬上产业道路,准备到杂货店买些纸钱———我想的无错啦,她确定是歹查某啦,若是真正美满幸福,早就有人一路啼啼哭哭来点香烧冥纸啦,我早就知道,过去拢是骗我,骗我庄脚查某是莫?———这样边走边思索,猝然又是一阵鼻酸袭来,根本听不见后面的叫唤声。
“这就怪了,如果不是家属,那又受到什么刺激?”检察官扳回脸,朝着躺在地上的他溜了一眼,“张法医,你好了吗?找到什么问题?”
一直在他身上捏捏揪揪的瘦高家伙站了起来,看着刚刚填写的资料说:“生前落水,外伤只有一处,但是伤口并不深,研判起来不足以致命,而且看起来不是钝器所伤,应该是水的冲力太大,撞到石头。”
“既然现场都找不到打斗痕迹,陈尸处又是要涉水才到得了,这不就是自杀吗?”
“检察官真是英明。”
“那就好了,村长,村长,你那块白布拿过来把他盖上吧,太阳快出来了。还有,那个谁?张警员吗,查出来了没有?”
被叫唤的警察刚刚收了无线电,碎步跑过来,特地压低了嗓门,“报告长官,还是找不到死者其他家属,只有以前的管区打听出一个消息,他的太太十几年前早就跳楼死了。”
啊,那就叫救护车先把人送走吧。检察官蹙起眉,喃喃中收闭了嘴,转了身准备离开。这时一直躺在地上的、他的灵魂或者他的躯体,突然伸手扳住检察官移动中的腿脚,以致对方一个踉跄跌坐在云白的菅芒中了。人群中哗然一声响了起来。
如果可以表达,他想说几句话,他真的没有自杀。当时他清醒得很,既然明白再也回不到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也回不到多年前那些应该抢救的瞬间,最后当然还是要一个人孤孤单单自己走回来。那时醉意早就消了,只不过眼前还是一片漆黑,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竿尖上那红焰的香点突然开始抖晃,连竿尖下的母线也明显地发出绷紧扯拉后如同风刮过树梢的声音。他丢下一直握着的手竿,迅速抓起另一支的握把,拉力沉笃、游晃、来回挣扎,是一尾超级家伙,是让他苦守多年,一再想要突破先前纪录的大苦花。
现在他要说的是———它突然钻入石岩下的深洞里了,他惯用的一向只是零点八号的母线,如果强行拉扯必断无疑。因此,他希望检察官能够理解,也多么希望世人能够体会,那不仅是破他纪录的苦花,也是惟一能在高海拔、冷冽水域等等恶劣环境中存活的高山鱼种。因此他决定涉水而去,帮它打开缠乱的线结,而不愿只是任它永远卡在石缝中挣扎。有什么困难的结是解不开的呢?当然,情况是那么紧急,他来不及脱下鞋袜,水温冰冷到极度,如同导电般不断有刺寒的冰钻纷纷击入全身;但那真的是非常孤独寂寞非常忍辱负重的鱼种,如果还有机会表达,他多么希望世人能够理解……
只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走入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