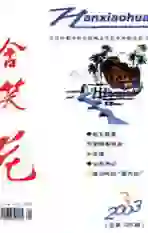舞者
2003-04-29陈洪金
陈洪金
我看见并亲历了我的乡村里的舞蹈,那些在大地上的舞动,把我引领到了一种不曾被修改过的境界,并且让我长时间地向往着,为那些舞步和神色而心潮起伏。我深深地体味到,在村庄里的田野之间的舞蹈,它所呈现的形式与隐藏的内涵,永远是我的叙述无法抵达的。
家乡的冬天那些此起彼伏的婚姻,给滇西北的雪山和峡谷带来了温情。我始终记得,我的童年曾经把我的经历放到一个小小的傈僳族山村里,涂上山村里的颜色。我的记忆在一个名字叫做撒巴子的地方,狭窄的山路在一望无际的灌木丛里时隐时现。红色的土壤斜斜地造就了一段又一段人生一样漫长的山坡,那些一年四季里都被树叶和花朵包围着的山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形成了种独特的氛围。山村里所有的耕种和采集都有自己的名称,就像他们以丛林里出没的动物们作为图腾的长长的姓名,把一个民族的全部含义,都交给了祖祖辈辈一步也不曾离开过的生老病死着的莽山深谷。还有那些舞蹈,从来都是延续着远古的狩猎时的姿态,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向着一个中心,燃起了希望和生命之火的中心,不停地围拢,不停地散开,粗犷脚步声和呼喊声,让一片树林边缘上的土地颤抖着,把一个旁观者的心震憾着。
我的幼年时期的一天晚上,在火光的照耀下,我胆怯地站在一扇低矮的木门旁边,望着一群人在泥院里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峡谷对面有呼喊声不停地传到院子里来,我不止一次在那些越来越黑的夜色里发现在移动着的火把,向着我孤独站着的院子里走来。院子里的篝火腾起了高高的火焰,火焰像热情一样灸烤着人们的面孔,照亮了越来越稠密的黝黑的笑容。歌声响起来了,伴随着舞蹈的节奏,一首又一首由古老的傈僳族语言创作出来 的赞歌,在古老的山村里,被那些舞蹈者唱出来,让他们的心灵不断地盛开、绽放。多年后,不经意坐在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我听到了渐渐远去的曲调,再后来,我才在一本书里读到了那些曲调熟悉的词语,发现了那天晚上的原声颂唱。那一天晚上,在简陋而朴素的山村里,人们一直在叙述着一个民族在滇西北的流浪 ,以及他们的祖先们所经历过的生活、苦难、爱情和感恩,叙述着他们的神祗在远古时期的战争与和平。
在那个宽敞的庭院 里,一对新人在夜色来临之后即将开始他们的夫妻生活。舞蹈在这一天晚上被四面八方拥来的族人们演绎着,依着一种古老的秩序,舞蹈和歌唱实现了一种对过去的追溯,对未来的向往。金色的火光烘干了滴到泥地上的汗水,尘埃四起,鞋子与鞋子不停地碰撞着,手牵着手不停地挥舞着,裙摆与裙摆在飘飞时摩擦着,歌声在火焰的升腾里带走了烈日与寒风曾经漂向村庄的艰辛。一对新人在父老乡亲们的注视下,开始了他们在火光中的舞蹈。新郎黑里透红的面色,让人看到他在山路上的许多艰辛的行走与跋涉,他粗壮的手掌,握住了他的新娘,火光照见了他的手,那些纵横交错的裂痕里,永远也洗不净的泥污,在火光里隐隐可见。新娘红润的脸庞被火光覆盖了她在白天的娇羞,微黑的被山里的太阳晒过的脸庞,微微露出的牙齿,淡红色的嘴唇,成为这一个夜晚最美丽的景色。一对即将走进他们崭新的日子的新人,在众人的簇拥下,没有发现一个孩子在远远的角落里对他们的注视。
在狂热的舞蹈外面,我不时地躲避着被人们的舞步踩得水一样溅起来的火星,一个孤独的旁观者。是的,他们的喜悦对一个孩子形成了一种回避与隔离,让我无法洞悉尚未对我敞开的生活。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在自己的生活边缘,偶然间才发现,在我的家乡旁边的那些小山村里,灌木丛所包围着的那些低矮的木头所堆砌而成的小屋子里,一个人们不曾体味过的生活境界,原来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夜已深,人未静。一扇门,对着山村里的所有的人敞开着,一双手,紧紧地挽着另一双手,不停地挥动着。沉重的舞步踩在泥土呈现出血液的红地上,激情四溅。火光渐渐暗去,火焰消失了,只剩下炽热的火炭,以堆积的形式留下院子的中央,陪伴着一个村落因为一对新人的狂欢。当我再也无法突破粘稠的睡眠对我的目光的围困,在院墙外面一个高高的枯草堆上,我渐渐睡去。梦隔开了我的惊奇和向往,人们渐渐离去的时候,我在枯草堆里向着一个神秘的梦境深深地下潜。一个人,让我心醉,一条路,在我的心里留了一种甜蜜的渴望与想念。从此以后,我渴望一场舞蹈,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的某个地方,也会为我而举办,我渴望一个女子也会在众人的围观中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在火光中随我起舞,就像那山村里的一对新人一样。
一次离开,注定了要让我从此再也不能抵达。
我的舞蹈总是在灯光的旋转下开始。我的情绪,却总找不到一个宁静的地方,让我的目光和心情都进入陶醉的境界。在城市里的某一个角落里,我的影子留在那镜子一样光亮的地板上。有人在唱起了首仿制的歌,一阵香气汹涌而来,我把一只手探过去,挽住了一个女人华丽的腰,慢慢地在她那一片放荡的目光中沉沦下去。在酒意中,我们总是在漫不经心地说着无聊的话,一种无耻和罪恶,远远地站在我的感受所不能触及到的边沿,不动声色地窥视着我。嘶哑的音乐不止一次地响起来,我发现一张网高高地扬起,把时光的心情尽数收去,让人只剩下一个不停地运动着的躯体,茫然地走向一个不知所终的地方。
伴随着我的脚步不停地移动着的女人,一次次让我感觉到了她的身体。热气透过她华丽的衣服,源源不断地向着我的胸膛传过来。在暗暗的灯光中,被许多种色彩轮流泻染过的目光,在不知不觉中蛇一样缠绕过我的颈项,一种麻木开始了它的旅程。空气渐渐地热起来,一个女人,把她的隐隐若现的乳房,只有遮住它不曾遮住的肉色,向着我的胸脯试探着抵过来。那种温热没有遮挡地呈现出一种欲望,柔软的肉体,开始了无动于衷的诱惑。缓慢的舞蹈,失去了它最初的章法和规律。在城市的角落里,在人来人往的地方,紧紧抓住了我的臂膀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曾经是谁的女儿,我也不知道她将会是谁的妻子,我更不知道她还会是谁的母亲。在一个陌生的日子里,夜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踩着胡乱的舞步,闯进了我的怀抱,把一对乳房向着我的领口奉送。
时光继续在丧失了羞耻和理智的道路上行进,一个女人的存在,在夜色里让我感知到的还有充满了血和肉的躯体。那披挂着一层衣服的肉体,丝毫不吝惜她的舍与。舞蹈的纷乱和沉迷,在暗暗的灯光下,渐渐地把她的大腿靠过来,把她的腹部贴过来,没有一丝忧伤和触动。我承认一种诱惑曾经引领了我的挺拔的欲望。那游离的嘴唇,渐渐地张开了她的深渊。但是,仿佛一个声音同时也在我的心灵里高高的夜空中,提醒我越陷越深的沉沦。当我慌乱地离开所谓的舞蹈着的人群时候,离开的脚步,挡住了我最后的沉沦与迷失。一个声音高声地告诉我,我始终在深深地爱着一个女人,那亲爱的身影,一天又一天地守着我用多年的心血亲自命名和垒筑着的家。是的,我一直珍爱着一个成熟而健康的女人,她一直珍藏着一个为我而保存着的肉体。于是,我无处诉说的惭愧与内疚,让我在城市里失去了往昔对舞蹈的向往,虽然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叫做撒巴子的山村里狂热的舞蹈,长期以来一直被我所向往着。
在我的滇西北,一个金沙江边的小县城始终很小很窄,它的存在却没有拒绝舞蹈以独特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夜色来临的时候,在我匆匆的路程上,同样也会发现小城里从来都不曾消失过那些舞蹈的身影。街道旁边的窗口贴上了各种各样的彩色塑料纸,沙哑的歌声就着那些颤动着的灯光昏暗地传到我的耳边来的时候,我会想起一种舞蹈引发的沉沦。舞曲不停地响着的那些灯光昏暗的地方,窄窄的门口,有人正在走进去,有人正在走出来。灯光把一些缓慢地移动着的身影映到窗口来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些人所拥抱着的身体和歌。夜深人静的时候,小城里的歌声还会在我们夜里睡醒的时候传来,呈现出小城渐渐现代化的夜生活。我知道那里的歌声在怎样漂荡着,人影在怎样移动着,躯体在怎样磨擦着,目光在怎样猜测着。但我始终对山村里的那些舞蹈保存着一种绵长而强烈的遗憾,但是由于在小城里的居住,我更愿意把我的想法和挚爱,交给小城里属于我的简陋的家,以及一个善良而朴素的女人。没有专门为我而跳动的舞蹈,没有祖传音乐,我的文字却寻找到了一个宽敞的世界,让我记录所有被我的目光注视过的面孔、纸张、感激、悲伤、树林、山冈、水流、花朵……
原来,舞蹈竟然也会成为一种遗憾,作为舞者,我无法告诉谁更具深刻的体味与经验。我至今都在怀念着一个叫做撒巴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