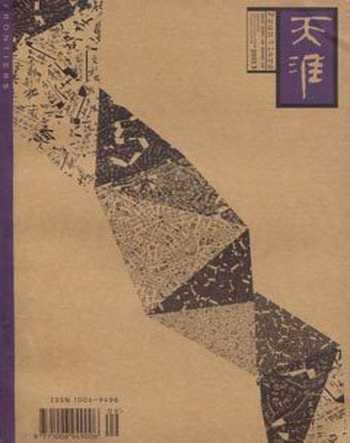音乐反战:从乌托邦到异托邦
2003-04-29颜峻
颜 峻
艺术家通常不大喜欢社会的既成规则。虽说忙着创作和享受人生,没有工夫带头跟权威作对,可是一旦事情变得热闹严重,激发起了责任感和激情,那么平时随心所欲,蔑视主流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习惯,就会爆发出来变成社会行动、政治事件。音乐家反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
当然音乐家还要看是什么样的音乐家,古典音乐家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从政府那里得了好处,再说跳到街上去又会弄脏了燕尾服;流行歌手通常没心没肺,以娱乐大众为己任,怒火太盛、观点太多,会坏了甜蜜无知的好形象;最后剩下的,就是青少年亚文化里面不安分守己的那部分,摇滚乐、爵士乐什么的。是的,爵士乐也很猛,美国民权运动那时候,黑人萨克斯手Archie Shepp这样解释自由爵士的突飞猛进:“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全国都在为消除非正义和卑鄙而战……炸飞了三个孩子和一所教堂,必然要在某种文化艺术的形式中有所反映……我们当中死的人太多了。”
先是民权运动,然后是反战。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美国够热闹的。1960年代末,全世界的学生都在街上游行,法国五月风暴,巴基斯坦全国罢工——四个月推翻了军事独裁政府……通过激烈的政治表达,年轻人和大范围的民众找到了一种自我形象,反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外化。这个文化的核心,要从反战的另一面来看——当观众往大门乐队的舞台上扔的大麻足够淹没脚面;当吉米·亨德里克斯为提莫西·利瑞演奏贝司,让这位哈佛教授一边传播LSD和精神旅行法,一边吟颂诗歌和竞选加州州长的声明;当公认的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被更感官的摇滚乐挤到一边;我们应该明白,“要做爱不要战争”的本质是做爱,而不是反战。
虽说在艺术家、音乐家的传统里面,充满着自由、天真的因子,但要不是和青年亚文化结合起来,也不会有新的激进传统。做爱也罢,反战也罢,都在摇滚乐、抗议民谣、自由爵士这些1960年代前后兴旺起来的新形式里找到了带头闹事的例子——以至于,后来的大众文化里面,不带头闹事的摇滚乐多少都显得有点不真实。这种态度,可以看作对主流文化的主动的对抗,或者干脆说,年轻人为抗议成人世界,而找到了一个姿态的合法性。这也是青年文化强调道德感的原因,在一个越来越技术和实利的世界上,道德属于青年,而不是老人。所以当艺术家传统和愤青传统结合起来的时候,各种浪漫的声音都会出现,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环保、信息解放……凡是政府做的坏事,或者说凡是既有权力体系犯下的错误,都会被加以挑战。所以说反战并不重要,而做爱才是永恒的颂歌——人性的、生命力勃发的、欢乐的、在热量的释放中生成快感和新事物的……
如此说来,麦当娜在新专辑上市前所做的反战姿态,比如说“我不反对布什,也不反对萨达姆,我反对战争”,听起来是高明的和平主义,但其实旧了,所谓妇人之仁,只能让提香时代的画家们叹息,而不能让今天的随便谁醒悟。反战要是没有理论背景,那还不如和尚来得干脆。而和尚的理论背景,又不是一个杀戒可以解释得了的……
前些天中国学者分头反战和挺战。反战的把萨达姆政府当作善良的弱者,挺战的,把美国政府当作正义的使者,旁边评说的,则表示只有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会不理会国家利益,一味强调生命的价值。是啊,这是一种不实际的、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梦想,它曾经在上一次反战潮流中盛行。但是自从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大麻非法以来,乌托邦草药、乌托邦音乐和乌托邦信仰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约翰·列侬变本加厉,跟他的艺术家老婆小野洋子一起脱光了给记者拍照。小野洋子说,让某某来和我做爱,他就会放弃战争。后来传唱甚广的《给和平一个机会》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思维方式不一样,音乐家,就是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实用主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知道呼吁那些心里早就有谱的政治家放下屠刀。音乐中自有宗教和哲学情怀,看起来乌托邦脆弱得不堪一击,实际上却改变了人心和文化。
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组织化和暴力,两者都不在音乐家的思维方式里面,尤其是前者。但世界早就组织起来了,当U2乐队高唱《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的时候,并不打算劝说英军和爱尔兰共和军拥抱起来;十年以后他们跑到波黑战争的战场边上开演唱会,也不是代表联合国向军队施压。以无组织对抗组织,以不实用对抗实用,最终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胜利。和平与爱并不存在于任何政府的章程之中,它在心里。音乐要无数次响起,在无数个具体的时间地点,对无数神经元进行微不足道的感染,经过漫长的遗忘和积累,最终相加,才得到了世界向善的可能。
作为乌托邦的升级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后来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倘若非要万众一心去实现,就需要组织起来,其结果就是《1984》或者红色高棉。但音乐家喜欢做梦,并且亲身实践局部乌托邦,他们喜欢做爱多过喜欢组织起来。即便是最危险的帮派说唱乐,也不会去参加政府组织。通过音乐,人们实践着童心、任性、友爱,对这个要求我们组织起来然后竞争得你死我活的世界进行瓦解,几十年以后,异托邦就出现了。这是一种描述,而不是实在的事物,它提供了一种现实社会中可能的存在,也就是以生态学的形状,以不同于金字塔的结构,另行发展一个亚社会、一个无形的地下世界。它外化为年轻人自发的公益团体、非赢利自由媒体、无政府主义研究会、黑客和网络社团、遍布全球的地下音乐传播体系、艺术家社区、互助公社、各种亚文化圈,但归根结底,异托邦的存在,还是依赖于人心的联接方式。
在2002年10月的“不许以我们的名义”反战集会中,美国人继承了西雅图暴动和热那亚行动的经验,又一次联合起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政治诉求的人士和团体,促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行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学者有乔姆斯基、萨依德和沃勒斯坦,诗人有W.S.默温,演员和社会活动家也不在话下,值得一提的,是从“感恩而死”的贝司手到前“愤怒反叛机器”的主唱和吉他手,从hip-hop联合组织到布莱恩·伊诺这样的老炮——顺便说一下,伊诺在世界杯期间大骂职业足球,说这是政府消耗人们精力和抑制大脑活动的阴谋,其激进锋芒不比愣头青朋克差吧——音乐家尽管没有当年独当一面、呼风唤雨的风头,但却在一个临时的集体中,呈现出没有界限的文化渗透景象。
当然,要说玩音乐的都热爱和平,那也不尽然如此。要不怎么会有死亡金属、撒旦金属之类乐队的盛行,又怎么会有欧洲的早期右翼OI朋克(或者今天法国的种族主义朋克)?死亡金属歌颂战争,是出于美学上的幻想,是一种舞台表演的仪式,况且他们还有巴西的Sepultura这种无政府主义乐队,连单曲封面都是学生运动。即便我们深入研究几百支歌颂战争和死亡的金属乐队,也找不到一支赞成实际战争和暴力行为的乐队,事实上,这更像是神话美学的再现。而右翼朋克乐队,因为更直接地通过音乐来表达政治态度,已经成了小小的灾难。美国的朋克领袖“反旗”主唱说过,那些打着美国国旗蹦跳的朋克真让人恶心——当民族主义混进朋克文化圈的时候,别说平等自由受到了威胁,就是战争也立刻多了新的靠山。
音乐并不是天堂,因为人们需要摆脱恐惧,需要欢乐和归属感,音乐才有如此的魅力。那些搭音乐的便车上路的思想或态度,其实本来就是音乐的一部分——既然“小红莓”唱过《僵尸》这样的反战歌曲,你就无法想象他们会像小甜甜那样做循规蹈矩的庸俗音乐。有的人生来反叛,唱歌不唱麻醉歌,做人不做哈巴狗,你说他喜欢做梦,他说他不孤独,还欢迎你加入。不管有没有反战的词,这就是反战的音乐,而反战的细胞,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缝隙。
当U2乐队的主唱Bono开始到处跟政府高官握手,劝说他们减免贫困国家债务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在大赦国际的活动中签署请愿书的U2乐队了——我要说他们的音乐从1993年以后变得越来越难听,形象越来越像从夜总会混到跳舞俱乐部的黑帮老大,和所有中产阶级肥猪(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刚出名的时候,爱尔兰人的看法)一样喜欢炫耀他们的迟钝平庸。我不想得罪人,说握了白宫高级助理的手就会丧失创作灵感,但是好心人Bono的确已经从江湖上跑到了朝廷——为了美好的目标——同时也的确丧失了创作灵感。他要靠加入一个体系,来实现善良的目标,或者说,他微笑着和有钱有势的世界打成一片,这样的代价换来了许多人不死于饥荒。这是值得的,但同时就音乐而言,他所从事的那种音乐,却断无与权力并存的可能。
据说“愤怒反叛机器”乐队的成员,有人在南美打过游击战。这种方式对于改变世界来说,成效并不显著,所以按照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大家还是去白宫跟人握手比较好。即使要反战,采取游击战士的方式、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方式、无业愤青的方式、朋克和其他无权者的方式,百万人相加,也不如一两个政客管用——如果他们打算反战的话——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异托邦是干什么用的。即使不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做爱,也不是简单地为了反战,或反别的什么。反对,总是为了维护和支持什么东西,否则岂不是弱智。但如何反对,在1960年代结束以后,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那些不想和高官握手,也不想仅仅游行的人,既不能加入自己反对的体系,也不能用对方的方式去对抗——这正中了人家的奸计,对吧,反叛的假象对于平衡社会关系、释放敌对势力的情绪有好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反主流文化的消费,来消解对方的——异托邦要的是建设,同时,改变权力的结构,结束用好官代替坏官、用好政府代替坏政府的思维方式。
这时候,上街的人、游击的人,就比通过关系减免很多亿美金债务的人更深刻地改变了地球。这话听起来有点太理想化了,但是道理一点都不错。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的人民,急着要民主;饥荒国家的人民,急着要吃饭;很多人没有力气高瞻远瞩。但我们还是要高瞻远瞩,谁说只有经历了充分的民主的人才会去反思资本主义?谁说伊拉克人非得从血海里游向彼岸?人们总是在不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强行提供凑合方案,而不是做点更复杂曲折需要耐心的事情。这就是权力结构的机制。而它的终结者,要比乌托邦的信徒、头戴鲜花的天真青年更当代化,要比靠恶作剧来种植想象力的雅皮士(青年国际党人)更脚踏实地,他们所做的最无用的事情,比如说游行,也可以将自己团结起来、鼓舞人心、就地发明节日和亲情。这样一来,新兴的美利坚帝国所依赖的思维和文化,就受到了根本的挑战。
同时,作为反面的例子,美国放克音乐老大,黑人詹姆斯·布郎在2003年的战争期间,给美军炮灰送去了四百张自己演唱会的票。他说:“我是穷苦出身,后来能够成名,作为艺人,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的荣幸,我会尽我可能地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为国出力。”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知道,一个帝国,是多么需要盲目的幌子,把人们装进集体,组合成软硬的机器。倘若他脑袋里没有那个庞大严密的国家呢?倘若他脑袋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而不是金字塔呢?倘若他已经经过了基本的去中心化改装,不觉得美国兵就比伊拉克人更亲切?
对比朋克音乐和放克音乐的美学,对比实验电子乐、自由爵士乐、愤怒摇滚乐和放克音乐的语言,对比进步的音乐和乡村音乐的道德观,答案就在眼前,它不在风中飘荡。
颜峻,音乐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地地下》、《内心的噪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