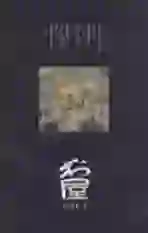也谈“穷而后工”
2000-06-14马俊华
马俊华
古诗读多了,就发现自己有这么一种倾向:喜欢那些充满人生失意情绪的诗篇,如渲染沉郁、伤感、悲痛、无奈等。至于那些欢乐或闲适的诗歌,读起来总觉得轻飘飘的,没有重量。相反,这些失意的诗篇写得都那么到位,里面似乎有一种勾魂的力量,能触摸到心灵深处那些黑暗隐秘的地方。孤独寂寞的时候喜欢读这种诗,心情愉快的时候也是如此。难道我的这种读诗法是一种移情?表明我有一种“为读古诗强说愁”的少年老成的心态?可扪心自问,我还没有衰朽和落魄到这种地步。当我把自己的这一趣味倾向告诉给知心朋友时,他们也都像突然发现了自己似的,脱口应道:“我也是这样!”再看看两千多年来那些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也大多是这样风格的东西,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等等。
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诗歌就能打动读者的心?难道人生失意是一种普遍现象?或者说这种失意里面藏着一种更普遍的意味,而这种意味是生命的底色?不管人生快乐与否、幸福与否,都是在这种底色上发生的?它和人们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无意识的基本人生体验是根本相通的?
我们不妨先看看“穷而后工”的提出者欧阳修的论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鱼虫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叹其奇怪;内有幽思感愤之郁积,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在这里,要是把“穷”理解为仕途的失意,明显是囿于中国古代的具体现实。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向主张“学而优则仕”,很多精神生产活动,诸如文学艺术并不独立,不能成为文人实现自己独立价值的途径。文人的路子很窄,只有一条仕途。古人所谓的“出世”和“入世”两种选择,实际上只是“出仕”和“入仕”两条道路。这样,能否做官就是衡量文人“穷”与“达”的主要标准了。由此可知,中国人的价值视野是很单一的,即所谓“上德立国,中德立功,下德立言”。文人的价值就是做上大官,侍奉皇上,治理天下。用李白的话说就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穷”实际上并非只指仕途的失意,而是泛指一切人生的逆境。
可在人生的逆境中,诗人只是“兴于怨刺”,抒写失意后的“孤愤”一类“人情之难言”的东西吗?确实,在失意的逆境里,人们会有“孤愤”的情态,会对现实表现出种种不满,写出“牢骚”一类的作品。可采取这样的方式去抵抗现实中的种种既成的黑暗或不公,恐怕并没有真正的自我说服、自我支撑的力量。要想真正维护自己,我想,必须获得一种更为真实的洞见,这种洞见能够重估浮生所追逐的种种价值,揭示出其虚妄的本质,否定它们和真实生命的必然联系。
可这样的洞见是什么呢?循着“穷而后工”的思路,我不妨继续剥离下去:功名他没有,富贵他没有,爱情他没有,生活的稳定他没有……这样一层层剥离开来,剩给他的,就是一颗不死的心,面对自然那四季更迭的变换,人世那盛衰浮沉的运转,纠缠牵挂。经过这样一番减除,生命可能就回到了它的根底处,余留下来的东西就是纯粹的个人和世界了:赤裸裸一条身子,从无中来,到无中去,空有一场幻景幻情。
在这种根底处里,生命作为一种活动,被完全纯化为灵性的体验,从来自自己和周围的变化中,感受着生命的流逝,和自己对生命的深情的依恋。这样,人就是最后的惟一的个人,世界就是最后的完整的世界,彼此都承担着对方的整体。在这样的体验里,人作为一种活物,享尽了风情万种的敏感和痴颠,这是他充盈的一面;作为一种活物,他同时感受到无物永驻的必然结局,这是他虚无的一面。纯粹的生命是什么?不就是敞开自己,应对来自自然、社会的种种遭际而获得的深广感受吗?这种感受自然要包括人生的负面的内容。由此,我生出一个想法:人在快乐幸福的时候,自己就被蒸发了,消失在那些如愿的“拥有”中了,诗情似乎也就随之消失了。只有在孤苦失意的时候,才能抓住自己,写出真正贴心由己的诗歌。
因为获得了这样的生存体验,他的视野就拓宽了,生命的体验就变纯了,一切都在更大的背景下被重新审视,切身由己的东西便水落石出了。生命因为转向这样的关怀而得到了充实和抚慰,人是天地间的人,天地也是人的天地。相比之下,种种浮生所追逐的种种功名利禄,其牢固性和真实性不就是不攻自破了吗?除了虚妄和片面,还有什么特征呢?可芸芸众生就是抱着这虚妄和片面的追求,而避开了生命根底的真相,强演这人生的戏,不是过于偏狭和滑稽了吗?
这样的人生体验,不就是我前面设定的那种洞见吗?确实,只有这样的洞见,才会对失意的诗人产生一股来自根基的支撑力量,才会对纷纭喧嚣的繁华场面表现出拒绝的态度和勇气。可以说,这样的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人心灵的减震带。当他们仕途失意后,都能从阅读和写作这些诗歌中得到安慰。因为在这种虚无空幻的人生情绪里,仕途的得与失最终算个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这样说来,“穷”是一种人生的契机,“工”是在诗歌中对生命的至深体认,是用生命的最终真实来支撑和说服自己。
这种跌落有被迫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它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获得的,而是通过具体的感受介入的。实际上,总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天生就有一颗“大心”,里面空空荡荡,人世间一切具体的“拥有”和“事功”都喂不饱、填不满它,只有那种丰富深切、完满全面的人生感受才能安抚得了它。当然,由于生活在中国古代那种“官本位”的社会里,这样的人也受到了这种“仕途价值”的影响,错误地把自己的“大心”的失落感理解为“仕途”的不得意。实际上,我们今天不难看出,像李白杜甫这种人物,不仅当不了政治家,而且连一般的管理者都做不好,因为他们性格中“乖戾”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如果把“穷”理解为“仕途”失意,把“工”理解为抒写“孤愤”一类“人情之难言”,则是肤浅的,也会错失其深层的意蕴,尽管这些人都有着求官不得的失意情绪。事实上,李白杜甫一类人物,他们转来转去,就是想跌落在这个生命的根底里。
人们常说,“文史哲”在中国是不分家的,这其实是极为虚妄的。中国的文史哲表面上相互联系,实际上是彼此分离的。尤其是中国的诗歌对生命感受的浅唱低吟,在很大程度上是游离于哲学、史学之外的。只有在诗歌中,才真正保留了真实的生命的呻吟。这种呻吟始终也没有在哲学上得到重视和清理,成为一种清楚的人生哲学。中国文学确实受到儒释道的影响,可这种影响的交汇处在诗歌中都是局部的,并没有成为覆盖整个诗歌写作的原则。在更大的程度上,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是基于自发的、直接的生命感受。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一边是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现实政治社会的主动迎合和投入,一边是内心适应不了这种迎合和投入而在诗歌中寻找精神慰藉。
这种人生失意中的最终洞见,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发生的,而是在“穷”中自守时频频出现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以为它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辟谷”状态。这样的洞见,其实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有限性的洞见。当生活走向深处时,在随之浮现上来的种种冲突中,就暴露出这种有限性。在短暂性和永恒性、此岸性和彼岸性、现实性和超越性、流逝感和驻留感一类冲突中,我们都可以意识到人生追求中那些最终不可逾越的各种鸿沟,这正是生命的有限性的表现。对此,人们只能接受,无法拒绝。
对于人生的有限性,中国人通常采取了隐忍静受的接受态度,西方采取了积极迎对的接受态度。李后主的词,杜甫的很多诗歌等,都是这种中国接受方式的典型。至于散见于中国诗歌中的碎句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等等。在西方,最典型的是古希腊悲剧。在《俄狄甫斯》中,俄狄甫斯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能解开斯芬克司之谜,可就凭着这种聪明,他犯下了弑父娶母的罪孽。这就是人的聪明智慧的局限性,它抵抗不了命运的安排。当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积极进取的时候,反而走向了人生追求的反面。这样,俄狄甫斯就“被生存的真相刺瞎了双眼”。
由此可以说,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是虚无情绪,其具体表现主要是感伤和无奈,西方诗歌的基本特征是悲剧精神,其具体表现主要是痛苦和绝望。这两种特征只是对于人生的基本点的不同态度,这个基本点就是人生的有限性。态度的不同,其实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差别,因为它们都是对空虚本身的认同和持守,对生命的负面的痴情拥抱。
其实,人生这种有限性,也即虚无情绪和悲剧精神,是充分地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里的,像生死寿夭、祸福得失、喜怒哀乐、时序流变等等生活经验,都渗透着这种暗示,只不过隐显程度不同罢了。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或多或少地对它有所经验和觉察,这构成了人们喜欢阅读和认同那些“失意诗篇”的经验基础,而一旦读到了这样的作品,就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共鸣,觉得心灵拓宽了,生命隐秘的一面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