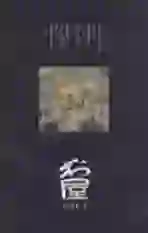长者的风范
2000-06-14丁东
古人说,转益多师是吾师。我从青年到中年,一直在太原,虽然也注意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但真正遇到高人,还是前几年定居北京以后。认识了一些饱经风霜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大家风范。无论做人做文,都受到很多教益。
一九九五年底,我认识了李锐先生。当时,《东方》杂志要搞一组关于顾准和《顾准文集》的专题,副主编朱正琳来电话,咨询找谁组稿合适。我在一次会上听柳萌先生发言,提到李锐向他推荐《顾准文集》,于是想到找李锐先生组稿。这样认识了李锐先生。李老一生饱经风霜,年逾八旬,仍然精神抖擞。我很难用一个定义概括他是什么“家”。可以说他是史学家,他有《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等力作,当时还在为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志每日伏案工作;可以说他是水利学家,在三峡问题上他自成一派,写了许多文章,集成《论三峡工程》;可以说他是诗人,他在秦城监狱中用紫药水写的《龙胆紫集》曾传诵一时,连胡耀邦晚年都把自己的诗拿给他修改;可以说他是杂文家,从延安到五十年代,都是杂文圈闻名的高手。李老则说,“我是一个杂家。”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他先后担任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和胡耀邦等领导人都有接触。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不但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也是青年一代了解党史、国史底蕴的入门书。他有诗云:“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前一句可以说是他的切身体验,他就在延安“抢救运动”和文革中两次坐牢;后一句则是他的毕生追求。他曾经对我说:我父亲是第一批同盟会员。虽然他去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很小,但他的追求我是理解的。二十纪发生的变化我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的一生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我们应当弄清中国本世纪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开国以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实教训太多,要把毛泽东的晚年讲清楚。马克思的理想从来是真正自由的,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物质的自由。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战争问题、发展问题、贫富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矛盾的问题、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是又乐观又不乐观……
李老对我最重要的启发,是有一次邢小群和他说起我的遭遇,他只说了三个字:“要做事。”这三个字太重要了。人在一生中,遇到各种坎坷是难免的。怨天尤人不行,等待顺境再做事也不行。只有抓紧做事,才能在社会中重新站起来。李老八十一岁的时候,说他九分之一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延安一年,秦城八年,要说我遇到的坎坷,比起他来,真算不了什么。李老这么大年纪,每天笔耕不辍,写的比我们后生晚辈还多。想起这些,对我永远是鞭策。
因为邢小群的一项写作计划,我还认识了萧乾、钟沛璋、李慎之、曾彦修、吴祖光、温济泽、戴煌、邵燕祥、朱正诸位先生。和这些坎坷半生的老右派们交谈,听他们述说自己的经历,就会更加痛切地感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是印在纸上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右派当年的情况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当时本来没有什么异端思想,打成右派纯属冤枉。有的则当时就触及到体制的弊端,比如李慎之思考的还政于民,戴煌批评神化与特权,吴祖光批评的组织制度,都打中了要害。中国的思想解放,本来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场反右运动,使中国从此脱离了人类文明的轨道,向着专横、野蛮、愚昧、黑暗的恶梦滑去。一觉醒来,已是二十多年之后,被人类文明的进程甩下一大截。这些老先生,饱尝人生的苦难,反思都很彻底。
我第一次见萧乾先生,是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那天我写的日记记录了见面的经过——
朱正来京,住李锐家,余前去探访,说及小群写右派事,他说萧乾可访,我说不认识不便打扰。他说萧就住附近二十一楼,可一同前去看望。
过了马路,便是萧宅,按铃后,开门的正是萧老,身着背心、短裤,把我们引入书房。书房中光线较暗,堆满各种中外文书刊。坐定后,萧说刚写了三篇文章,都是千字短文。我感谢他为我和一位朋友编的《王蒙现象争鸣录》写书评。他问我作什么工作,我说在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个题目很好。我说,写了一篇《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谈夏、巴、冰、萧的晚年,萧说,我不能和他们比。朱正说我写了《逢场作戏的悲哀》,谈郭沫若,很尖锐。萧笑着说,我要感谢郭沫若。四八年他一篇文章,解放后我就成了右派,到文革中,右派是死老虎,受冲击小些。吴晗、千家驹原来是左派,文革他们受冲击更大。萧说,还有一篇文章是谈讽刺文学,讽刺文学是作家关心社会的一个尺度,也是检验政府是否开明的一个尺度。现在政权这么稳固,何必害怕讽刺。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发表不同政见是常事。不允许不同政见说明只有一种政见。我也不愿意乱。他还谈到胡耀邦,说当时胡耀邦代表党向知识分子承认错误,大家的气也就消了,还是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最好。他问朱正来京何事,朱说参加“民进”的会。他说,“民盟”开会我是不去参加了,政协开会我也不去,去就是干这个(他比划了一个举手表决的动作),有什么意思。“民盟”有个杂志叫《群言》,我原来就是搞言论的,现在哪有什么群言。
这样和萧乾先生就认识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晚上,文洁若老师来电话说:“萧乾不行了,你来看看吧。”我听了一惊。前几天,从电视新闻上还看到庆祝萧老九十寿辰的消息,怎么突然就倒下了呢?
第二天,我赶到北京医院才知道,由于肾功能衰竭,萧老已经昏迷四天了。我拿出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反思郭沫若》。萧老的儿子是两天前从美国赶回来的,他一看标题便说,我爸爸要是能看到这本书就好了。我也扼腕叹息,晚了一步,这本萧老关照过的书,竟没有让他看上一眼,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认识萧老三年多来,和他谈过十来次,虽然他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但共同语言很多。我当时开始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这正是萧老晚年思考的重心。文老师说我是他的忘年交。九八年春节,我去萧老府上拜年,谁知萧老已经住了北京医院。家中无人,我只好把一本刚出的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小书《和友人对话》留给邻居,请代为转送。第二天就接到萧老的电话,欢迎我去医院一叙。文洁若老师在旁边特地嘱咐,来医院就是谈谈,千万不要买水果鲜花。我在病房刚坐定,萧老便谈开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思考。他说:我认为读书人与知识分子不是同义语。文盲当然不可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读过书。然而光闭门读书或埋头作试验,不问世事,那仅是读书人,但还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读书人。那样,他才有条件看书,看报,了解世事。但是,他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关心国内外大事,并有自己的见解。在一定场合,还会表达出来。若把国家比作一条船,船上有众多划船手。知识分子就得一边划,一边还高瞻远瞩,留意船的走向。解放之后,要知识分子做驯服工具,我当时听了心里就有一个问号。如果都成了驯服工具,我觉得对国家、民族前途未必有利。帝王时代的御史,大家都来给皇帝磕头的时候,他能够看得多一些,有时提些不同的意见。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良心、良知。反右除了对个人的打击以外,把知识分子能够起到的那种帮助政府警惕、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的“御史”作用也一同消灭了。现在大家都学乖了,绕着圈子说话,直截了当的不多。巴金提倡说真话,我想修改一下巴金的“要说真话”,我想加上“尽量”两个字,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说真话,别看简单的三个字,很难做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很知趣,能够和领导和平共处,上边对知识分子也不搞什么运动。人从本能来说都是追求一个平安,谁没事爱给自己找麻烦啊!国外遇到大事爱找一些言论界人士发表意见,咱们这儿可没这个习惯,知识分子也求之不得,你不来找更好。但是我觉得言论堵塞是很可悲的。一个国家如果只有齐声歌颂,而没有舆论监督,很可怕。
过了几天,他又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医院。原来,他给我的那本小书写了一篇评论《读丁东的〈和友人对话〉──兼小议知识分子问题》。萧老的提携,当然让我感动。但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晚年的精神状态。在中国的作家中,萧乾先生不是最高寿的,但坚持以知识分子的良知经常发出声音的作家,他却是最年长的。他还是像当年参与《大公报》笔政时那样,回应着国内和国际的风云。他对思想动态的密切关注,超过许多比他年青几代的作家。有关陈寅恪、顾准的书,他都看了,他还让我找来王小波的几本书给他看。他把医院的病房当作书房,笔耕不止,几乎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身上,我看到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到老也是变不了的。十日晚上,傅光明来电话告诉我:萧老去世了。我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思绪翻腾。他走了。二十世纪也要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接触的老人中,最有思想家气质的,是王元化、李慎之、朱厚泽几位。他们都担任过高级干部,但同时又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比起一辈子在书斋里生活的教授们,他们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为学术而学术;从政的经验使他们的思考更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穿透力。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紧扣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真问题,他们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种思想能力,不论到哪国留学,都是学不来的。比起一般退下来的老干部,包括那些二十年来站在思想解放前列,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他们又更有学者的气质。现实的政治层面和形而上的学理层面同时在他们的视野中得到关注,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还是西方现代的学问,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为我所用,这就使他们的表达方式超越了官场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种境界在领导干部出身的老人中又是很难达到的。
我曾和高增德先生一起提出过“南王北李”的问题。那是一九九六年,我到太原和高先生谈起学界有哪些人受到尊敬,一番讨论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小文章《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文章不长,只有一千字,文章说——
在当今文艺界,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满天飞,实际上很多是廉价的吹捧,甚至自吹自擂。学术界虽然也有泡沫现象,但更多的是听到一种忧患之声:世无大家,遂使小品流行!我们以为:中国之大,没有大家出现的慨叹,是以历史为镜,比如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大家、大师,的确是时间长河淘洗的结晶。社会公认多在事后,而不在当时。
但面对现实,大家风范,还是有迹可循。所谓大家,一是自己博大精深,有俯瞰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能在多学科领域自由出入,整合自如,学问超过同辈。二是开一代风气,学术与思想打通,文品与人品一致,影响力办辐射到各个年龄段。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文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风范,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
具体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我们以为,“南王北李”值得注意。南王,上海王元化;北李,北京李慎之。两位先生,一个曾是“胡风分子”,一个曾是“右派分子”;一个精于国学,一个擅长西学;都是半生坎坷,一腔豪情犹在。尤其最近几年,关注的问题颇为相近。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而且,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
五四时代,有“南陈北李”之说。其实,陈独秀、李大钊当时才三、四十岁。放在今天,乃是青年教授。他们之所以身孚众望,无非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手著文章”。试看如今之域中,与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气氛恰恰相反,犬儒之气太重,可谓“文章妙手多,道义铁肩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著书都为稻粱谋,则比较时髦。而王李二位,仍在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这就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勉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其实,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其心境,无非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二十世纪已近尾声。人们称这个时段为世纪末。每个世纪都有开头和结尾。可怕的不是进入历法规定的世纪末,而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的知识分子,沉缅于世纪末心态之中。南王北李,之所以在学界赢得敬重,就是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砥柱中流,与世纪末的颓风抗争。这种精神,正如王元化先生钟爱的一幅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当时与王元化先生还没见过面,和李慎之先生也不熟。只是参加《顾准文集》讨论会,和钱竞等聊起来,感到思想界没有带头的高人不行。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学界中青年中颇有人望,李慎之先生在北京中青年学者中也颇受尊敬,于是和高先生讨论,模仿五四时代“南陈北李”的说法,提出“南王北李”。这个说法,王李二先生都不赞成。尤其是王先生,认为我们提问题是着眼于立场。这倒是实情。但我在知识界遇见不少中青年朋友,对这种说法却有共鸣。于是,“南王北李”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
后来,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到上海拜访了王元化先生,交谈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他都要一一重新思考。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他还告诉我,八十年代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中央领导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八十年代,有这么一批有风骨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才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中兴景象。
李慎之先生原先有约法三章,不给报纸开专栏,不接受记者采访。邢小群访问他的右派经历,他一开始也不同意,后来看了邢小群对别人的采访,同意谈一上午,整理出来,又不同意发表。湖北的《今日名流》想发,我又找他商量,他才答应破一次例。原先,他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一九九七年出访德国期间中风一次,医治及时,恢复得不错,从此加快了写作速度。很多思想界有影响有突破的书,都找他作序。他住协和医院的时候,我请他为《顾准日记》作序,知道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先读原书,作卡片摘录,然后打草稿。他说,我写一篇文章,要用半个月。他在一九九八年,还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不再沉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以及未出版的《生活在真实中》中译本等作了序。这些序文,和他发表的其他言论,为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归奠定了思想座标。所以一经发表,备受思想理论界的关注。本来,他希望更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出来带头说话,未能如愿。这个头,只好由他自己带了。
朱厚泽先生在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曾任中宣部长,虽然时间很短,但他提出的“三宽” 至今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是东张西望,看一些书;东游西逛,有时间到各地转一转;人家叫我说,我就东拉西扯。最近北大百年校庆。大学是什么,大学应当是不断冒出思想火花的地方。路甬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写了一篇文章,说科学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好奇心。没有自由思想的空间,还搞什么学术?只注释经典,就成了经学。没有多样化,世界就不成为世界。多样化是世界的本源,单一才是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主张对不同的意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宽厚一点,把环境搞得宽松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不耐冲击,无论自然还是社会,冲击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保持一点柔性,保持一点弹性,有利于抗冲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三宽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大家都在讲,我不过讲得集中一点。理论是理论家的创造,文艺是文艺家的创造,党和政府无非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创造,替代是不行的,也不是当裁判官。项南生前参加十五大,原先中顾委的那些老将军还谈到赞成三宽。朱厚泽先生还从生态意识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角度来深化这个基本思想。他说,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压、“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 结构与功能是一对很重要的哲学范畴,过去限制在自然辩证法里,其实在社会领域、思维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范畴。现在人们喜欢说调整结构,但结构不完全是调整出来的。它是发育出来的。你真想得到她吗?那就着力营造她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自然生态如此,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如此。科学是自由思想开出的花朵,技术的不断进步则是市场经济竞争强化的产物。这并不妨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可以是绞刑架前自由思想的花朵;而技术的飞跃进步,不是市场而是战场、不是竞争而是战争强迫推动的产物。你真想让科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那就着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吧,那就切实推进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吧。否则,即令是花大本钱引进最新技术,也落不了土,扎不下根,难免不枯萎老化。世界不能用科学概括一切,除了科学理性还要有人文精神。作为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光有科学,还要有艺术。宗教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达,但人文精神不只是宗教,还有艺术、文学。在古代,艺术和科学与物质生产是相分离、相对立的,大部人从事劳苦的作业,才能腾出一部分人从事艺术和科学。这就决定了只有官方才能享受、占有艺术和科学,所以中国古代不提倡创造的艺术,只提倡工艺、提倡匠心。这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种缺失。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是多元、开放、和谐。多元是对一元说的,开放是对封闭说的,和谐是对斗争说的。这里既有人际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也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要再搞一个吃掉一个。什么人定胜天,不要轻信这些豪言壮语,我们都轻信过。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对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它始终处在不断地实践、检验、批判之中,扬弃旧的,发现新的,永无终止,永无止息。信仰则是人们对自然的心灵仰慕,对人生的感情寄托;对恶性循环的扬弃,对善的虔诚;是善良的人们一种内心的追求和一种感情的寄托。多年来,我们在对待科学和信仰的问题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科学变成了信仰,既不存疑,又不检验,提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公开宣扬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同时,我们又用科学去对待别人的信仰,批判别人的信仰“不科学”。这么一来,既毁坏了科学,堵塞了自己通向真理的道路;又毁坏了别人善良、虔诚的内心信仰,两样东西都给毁坏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元的专横的政治环境中进入社会的,是在目的论哲学的氛围中开始思考问题的,思想深处一直是受意图伦理支配的。朱先生提出的生态意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剂良药。
萧乾先生驾鹤西去不久,温济泽先生也与世长辞。温济泽先生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我认识温老时,他已年逾八旬。我对温老的了解,是先读其书,后识其人。其书,就是温济泽等著的《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为王实味平反,是温老晚年完成的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王实味的平反,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王实味不只是一起孤立的个人冤案,而是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遭遇革命的缩影。王实味到延安,本来是为了追求真理,献身理想,但他从延安也看到了与革命理想相悖的现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于是在整风中提出批评意见,因此被打成托派分子、反党小集团的头子,整风从此转入滥整无辜知识分子的“抢救运动”。一九四八年,王实味在晋绥竟被处死。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李维汉老,晚年反思一生的经历,感到他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发生王实味冤案未能澄清,是莫大的遗憾,于是在临终前托咐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温济泽完成此愿。温老接受李老的嘱托,与其他人不懈努力,终于在九十年代初通过有关部门,推倒了强加在王实味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使王实味的精神遗产,得以泽被后人。同时推动中国思想界反思的触角,向四十年代延伸。
我和温老只见过数面。最后一次见他,是一九九年三月四日。当时,戴煌等十位首都著名知识分子披露郑州冤案的长文刚刚发表,有一家杂志邀我访问几位知名学者,请他们就此事发表感想。温老和李锐先生都曾关注过这起令人发指的案子,他们又是近邻。于是我电话联系去采访他们。进了温老家,却看见他已躺在床上,讲话十分吃力。夫人钱老师说,早上接电话时还很好,刚才犯的病。没想到,这就是温老最后一次接受采访,这篇采访录,成为他公开发表的最后言论。四天后,温老就住进了医院。三月十六日,温老逝世。
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参加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排成长长的行列,挽联很多,在告别室外挂得满满的。印象较深的有:“九九八一难,留下真言,精选文集,广修传记,烈士精神永垂世;两个二十年,追回逝水,平反大案,不停笔耕,火山爆发逊于斯。”(李锐)“少年始报国,不屈不移不淫大丈夫,历经劫难终无悔,鞠躬尽粹;老耄仍磨砺,至诚至善至爱真君子,著写春秋亦自由,瞑目方休。”(郑仲兵)“写自然科学文章,写社会科学文章,黄卷苇编,孜孜全在求真理;为本身沉冤翻案,为他人沉冤翻案,丹心鹤发,苦苦无非要自由。”(郑惠)“言传身教,春风化雨,门墙桃李万千树;口播笔耕,鞠躬尽瘁,高山松柏八五秋”。(北京广播学院)这些挽联,概括了他的经历、人品和人缘。从他的自传中,可以知道反右的时候,他不忍心把无辜的下级打成右派,自己却被打成了右派。八十年代,他不赞成粗暴地批判不同的学术见解,自己却被推入自由化的行例。他虽然革命一生,但心肠不那么硬,人情味比较重,所以在官场上难以修成正果。温老去世之后,我在一个朋友家里遇到旅美女学者杨瑞。无意间提起温济泽的名字,便引起她的诸多感慨。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早期学生。她对温老的印象就是:领导干部中居然还有这么通情达理,不打官腔的好人。
所幸的是,温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完成了一本题为《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口述自传。我妻子邢小群三、四年前采访过温老,请他回忆过生平往事,知道温老这几年的思想变化。前几年,温老回忆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事情时,涉及到一些在世的或去世的要人时,还有所顾忌,嘱咐邢小群发表时一定要删掉某些人的姓名。但在这本口述自传中,他已打消顾虑。比如涉及到胡乔木,他既谈到胡对他的同情帮助,也不讳言他们之间晚年的分歧。我亲耳听到他在《百年潮》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起写作的心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人常说,思想解放无止境。其实,解放思想,主要是解放自己的思想。这本自传就是温老八十岁高龄以后思想解放新境界的结晶。外界有所不知的是,这本自传印出的还不是全文。有一章碍于目前的舆论环境,出版社请温老撤下。他体谅出版社的苦衷,同意暂时不发。温老也不想把他的想法藏之名山,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谈话时,还和我谈到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发表的问题。温老对党既忠心耿耿,又忧心忡忡。他的心愿,是希望后来的领导人,能够顺乎民心,顺乎历史潮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