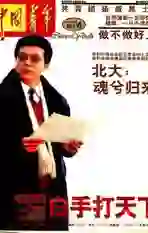媒体能救多少杨晓霞?
1996-08-28黄艾禾
黄艾禾
我想讲这件事,是因为我看到现在各类媒介上还在那么频繁地报道着各种各样的需要救助者,大报小报上还在一遍遍地呼唤着人们的爱心。
这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行刘女士给我讲述的一件事。这件事把她搅得几个月内心不得安宁。她向我讲完了以后,我同样陷入一种难以平息的内心矛盾之中。
刘女士讲述的故事
那是去年9月底的事了。那时我闲着没事,兼着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就是特别忙时约你打个下手。可是邻居小马把这看成是很了不起的事。有一天,他很谨慎地问我,他在生意上的合作伙伴W君想和我认识认识,顺便想向我反映点情况。他那种急切的口气让我觉得他要请我帮他好大的忙,我连忙解释说,我只是个理论版的特约记者,小马坚持说这没有关系,我就答应了。
两天后的中午,我看到窗外有一个陌生人在我住的楼前徘徊。后来小马把他领到了我的家,我才知道他就是W君,他怕来早了打扰我的写作,就在外面等了那么久。他们把一个记者的差使看得那么神圣,这让我受宠若惊,也有一点感动。接下来,他们表情肃穆地开始向我讲起小石。
小石既不是小马的亲友,也不是W君的的亲友,他是W君的老师的孩子,是一个才22岁、却已有10年白血病病史的小伙子。小石在12岁那年被发现患了白血病,从此,小石的一家人就开始了
漫长的艰难的与这顽疾的抗争。小石的父母都是学校里的普通教师,他们没有多少钱来付所需的高额医疗费用,但他们尽了自己所能尽的一切努力,想到了他们能想到的一切办法。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小石的父母并没有因此慢待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学生,他们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的奔波中从没有缺过一次课,甚至不曾迟到一次……w君说,我们非常为我们的老师感动,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救这个孩子。现在他的病情在不断恶化,据说只有换骨髓才行,但是做这种手术要几十万元的手术费!刘记者,最近我们从报纸上看了杨晓霞的事情,觉得有了希望,你要能在报纸上给写一篇,这孩子就有救了!
后来,小马搞了辆车,把我拉到小石的父母家去采访,又带我去医院看望小石,并为他拍照。与小石的那次见面让我终生难忘——他躺在严格隔离的玻璃罩里,面色苍白,头发一把把地在掉。可是他的神志极为清醒,情绪乐观。他非常平静地向我讲述与他同病房的和他得同样病的人是怎样一个个死去的,说“我这样就不错了”……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这样近地目睹一个人在走向死亡,这感觉特别难受,很长时间了,我甚至希望能把他忘掉……特别是后来,主治他的医生告诉我说,现在小石的病情已是晚期,即使换骨髓也没用了,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但是我还是开始写关于小石的文章,而且写得非常投入。两天后,我把文章写好了,送到了报社周末版。过了几天我在食堂碰到周末版的一个编辑,又打听这稿子,那位编辑很含糊地说看到稿子了,“现在这类稿子特别多”。
再往后,我离开了那家报社,到了一家杂志社。我再也没有听到这稿子的音讯。我想编辑肯定是不想用它了。但是我该怎么跟小马、W君和小石的父母解释呢?开始他们老给我打电话问这事,我就把人家怎么说的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后非常冷淡地说:“发不出来算了,咱们也不懂社会上的那些路子。”
后来,他们就不再理我了。我打电话找不到他们,我打传呼机他们不回。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小马来的一个电话,说小石的父母托他向我要回小石的照片和录音。我急忙问小石怎么样了,小马避而不答。我猜想恐怕小石已经不在人世了!
本来我与小石素不相识,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把我扯了进去。但是这些日子我无法摆脱这件事。一个人死了,而且是你眼看着死的。他在临死前向你呼过救,可是你没救成……我特别难受的是小石的父母的态度,就像是我骗了他们一样。他们当初强忍眼泪那么殷切地为我提供一切材料,现在是不是觉得被涮了?是不是觉得煤体所做的一切都是骗局,都是不可信的?
——直到今天,我无法摆脱这件事,我无法面对小石的父母,无法面对自己的职业,也无法面对自己……
重讲杨晓霞的故事
听完刘女士的故事,我一时无言以对。我可以安慰刘女士说,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了,他的死没有你的责任。可是——他死了。为什么他就死了,杨晓霞就活了?媒体救了杨晓霞,为什么没有救小石?媒体本身究竟有多大作用呢?它应该是起什么作用的?它能够救所有的人吗?
我去采访了救治杨晓霞的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在他们那里,我又重听了一遍杨晓霞的故事。
杨晓霞的得救的确是靠了媒体的宣传。在北京的媒体开始报道杨晓霞之前,杨晓霞的父亲已经带着她在山东跑了很多医院,在当地也搞过小型的募捐。但是,他们一家欠下的债务仍在一天天增加,晓霞的病情仍在一天天加重。他们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到了北京,找到他们的一位老乡——德州行署驻北京办事处的老邢。老邢是位复员军人,他说:“只有去找解放军了!”就这样找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住在了外二科。但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当时也没有办法控制晓霞的病,眼看她的两手在发黑溃烂,连脸上也开始出现了黑色斑块。出于对晓霞的同情,外二科的护士们自发地为她捐了一些钱,可是谁都明白,这点钱(大约2000元)是救不了晓霞的命的。
当时,杨晓霞的父亲已经绝望了。他已经花完了他能得到和借到的所有的钱,准备就带晓霞回家了。这时,老邢想到了新闻媒介。他找到了他认识的一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沈峥嵘,希望能通过报纸对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生护士们表示感谢。1995年1月15日,沈峥嵘的报道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篇幅不大,但这是北京第一篇关于杨晓霞的报道。
接着,是北京电视台介入了这件事。2月4日,正是春节的大年初五。从这一天起,北京电视台连续八天连续报道杨晓霞的事。报道震撼了北京人的心,也震动了北京的新闻界。2月6日,光是《北京青年报》就从不同方向赶来了不同部口的4名记者。到了2月中旬以后,各方面的记者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军区总医院,有北京的、外地的、香港的;有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杂志。根据北京军区总医院所留下的记录,参与过杨晓霞报道的媒体共达70多家,除了北京最著名的各大新闻机构,还包括有(中国律师报》《中国特产报》《北京邮报》《天文爱好者杂志》乃至“济南列车段新闻信息中心”这样不知名的媒体,至于转载过杨晓霞消息的新闻媒体,那更是无法统计。在采访的高峰期时,每天医院要接待十几位记者。据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庄副政委回忆说,当时为了保证晓霞能得到良好的隔离和休息,曾经几次和拼命要往病房里钻的记者吵了起来。
新闻媒介的空前报道使得杨晓霞的治疗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从军队到地方,从卫生部门到民政机构,各级
领导纷纷来看望杨晓霞。解放军总政群工部长邓先群、北京军区司令李来柱、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文全,乃至山东省团委、妇联、残联、民政厅、德州市、县、镇、村,各级领导全来了。
报道唤起了无数人的同情心。从2月4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报道的当天晚上,就有人来捐款了。第二天,来捐款的人就排起了队。医院为此开始设立专门的接待站,从每天早上6点值班到晚上10点,可是过了晚上10点还有从门缝里塞进钱来的。一笔笔的捐款从天南海北飞来,开始医院还都把它交到杨晓霞的父亲手中,后来钱太多了,杨父就要求医院代管。这时医院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钱是全国人民捐的,如果用不好这笔钱,就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要知道,捐钱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大款,他们每人汇来的钱数并不多,可是却是从他们的口袋里挤出来的。有的士兵把他们仅有的一点津贴夹在信封里就寄来了,因为他们的军营离城里的邮局有几百里路……就这样,一共是87万多元。这87万多元是这么一点点凑起来的!你要是乱花了,对得起他们吗?”庄副政委说。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由各方代表组成的“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
有了各界的重视,有了钱,杨晓霞得到了最好的救治。北京最好的中西医专家为她会诊,北京军区总医院提出的口号是,对杨晓霞要“一流治疗,一流护理”。杨晓霞的结局是大家都看到了的,虽然她的手指截去了几个,但她康复了。在人们的齐心努力下,她从死神的手中挣脱了,她回到了灿烂的人世间,回到了她的家,回到了她的亲人身边。
回述杨晓霞得救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没有媒体,就没有杨晓霞的新生,媒体救了杨晓霞。
在杨晓霞之后的故事
赵颖华,《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在铺天盖地般地“杨晓霞宣传大战”中,她是介入最深的记者之一。《北京青年报》周末版“救救我吧,我不想死”的6000字长文就出自她的手笔。由于她的多方积极参与,北京军区总医院特请她担任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中新闻界的代表。
谈到由于媒体的介入而促进了社会对杨晓霞的关注,进而拯救了杨晓霞的生命,而她正是这一拯救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赵颖华觉得很欣慰。但是,当我们谈到在杨晓霞之后发生的故事时,她的脸色阴郁了下来。
“其实,不光是我,我想参与杨晓霞
报道的许多记者都遇到了和我同样的情况——那次是我出差回来,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有一封信,说一定要我看。我一看,是一封求助信,是一个母亲写来的,她的孩子得的是‘法鲁氏四联症,是一种很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她没有钱为孩子治病,就请求我能为她在《北京青年报》上登一篇文章,像我们当初救杨晓霞一样救救她的孩子。这已经不是我收到的第一封类似的信了。
“我每一次接到这样的来信,心情都非常沉重。因为,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救他们所有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办的报纸并非只是做救助这一件事的,周末版也不是单一的救助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报纸每天、每块版都登的是救助内容,你说读者还会有兴趣看吗?
“从办报纸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道理很清楚,可是我无法面对那些病人家属讲这些道理。我对他们说,对于你们来说,家里的病人就是最大的事,可是我得面对那么大的读者群,得考虑读者的需求,对于他们,一个又一个这种事,就是重复了,也就不再会有杨晓霞那样的效果了……可是,这些话说着,他们也都很客气地说是啊是啊,可是,那无助的绝望的神情让你不忍心再看……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活得真沉重,觉得这记者的职业太沉重!”
我问赵颖华:“对于报社来说,什么样的病例是容易登出来的呢?为什么杨晓霞的事会有那么多的媒介愿意登呢?”
赵颖华给我分析了杨晓霞。首先,杨晓霞得的病是一种很怪的病,谁都诊断不了,这就非常具有新闻性;其次,杨晓霞这孩子非常可爱,她是村里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孩子,懂事,孝敬父母,特别招人疼,在媒介上亮相效果特别好。当然,在当时已经有许多媒介在炒杨晓霞的时候,会形成一种连锁效应,使卷进去的媒介越来越多。
在报道了杨晓霞之后,《北京青年报》对于同类的报道是非常谨慎的,编辑们心里很明白,短期内再掀起一个杨晓霞式的高潮是不大可能的,老搞这种新闻轰炸读者也就会失掉兴趣了。如果真的要做这类报道了,就尽可能地找一个新闻点。赵颖华说,前些日子他们的报纸为一个孩子呼吁过,那孩子得的是白血病,这并不是一种很罕见的病。于是他们就在孩子的家庭上做文章,利用孩子的父亲当年是位劳动模范这件事,号召大家来关心“劳模的儿子”。文章登出以后,收到了1万多元的捐款,离治病所需还差得很远。过了一个多月,孩子去世了,孩子的家长还对报社千谢万谢。“你说,如果宣传得有效果,我们心里也安慰点,如果是这种效果,人也没救成,那不是太难受了吗?比如这次这个‘法鲁氏四联症,我特意去请教了阜外医院的专家,他们看过病历后告诉我说,这种病况就是花上几十万元,做了手术,也改善不了多少。这样的话,号召大家捐钱,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赵颖华又说。
话说到这里,我觉得好像有点残酷。如果你的孩子得的是一种并不罕见却也能致命的病,如果他恰巧也不是劳模的儿子,父母也不是当年的战斗英雄,什么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都没有,是不是他就不能有上报纸呼吁救助的权利了?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又回到我们在一开始提的问题上:媒介究竟有多大作用?它应该起多大作用?它应该救所有的人?如果没救成,就是它的失职吗?
一时间我心里回答不了这么尖锐的提问。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飞速发展起来的大众媒介事业。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媒介已经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有关媒介本身的问题已经摆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我的同行们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而问题的答案,也一定在全社会都发展起来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