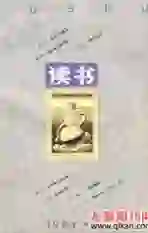必也正名乎
1994-07-15张士甫
张士甫
台湾诗坛漫步
我受《现代诗社》之邀访问台湾诗坛已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其时,《蓝星》停刊,众多诗刊百家争鸣,原先的三分天下已不复存在。——各社团诗人亦不断会串,一些声名卓著的诗人,比如杨牧,已超然于所有派别。台湾诗坛似已进入无序状态。
这是否预示着现代诗的更原始亦更现代的猎巫时代的到来?——并非个人意志的因应,却来自艺术社会的趋势。
于是我以我的习惯和观念,找到了一个流派,几个群落。——擅自划分了几个集群。——他们若听说彼此属同一营垒是否诧异?《易·系辞》说:“物以群分”。可见分是要分。却是这样分的吗?
五十年代初,在海峡的另一边,现代诗及其运动处于近似宗教的狂热中。
以纪弦为首的现代派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与余绪在台湾发展壮大的最具正统地位的诗歌流派。这时期的有关争论逐渐
这一流派有其先天性优势:
它扎根于民族的宏观诗学——禁令与压抑毕竟未起阻断作用,反而增强了它的吸引力。——由于地域时势诸因素与西方文化形成紧密关联。——没遇到类似“日丹诺夫”式的强力干预。——诗刊非官办,有论争阵地,宜于砥砺。——社会生活及诗人遭际亦非歧异多变。
然而大陆的长处恰为台湾短处:
它远离本土,难从风俗民情山水田园直接吸取精深的民族传统。地域狭窄,历史视野难免偏狭。另一缺憾是它的意识:忧患太少,日常生活的兴致过浓,遂难摆脱岛屿心态。因而窃以为,台湾诗大多纤
可见诗家之幸非全在人谋,亦由天时。——幸好它的背后是一个具有无限寓意的世界,是由人、社会、宗教组成的全息性大系统。
围绕着审美沉思这个核心,他们的情趣何在?其多样性和扩展性如何?——有无强烈的内在化和反艺术化倾向?在徜徉中思索中我才逐渐弄清我自己的问题。——一得之愚便差可作为此行之收获吧。
以写作为生命的诗人我找到三位:商禽、夏宇、零雨。
大诗人、领导风气与运动的诗坛班头:痖弦与梅新。
找到了或正在寻找自己的哲学位置,可能成为天才诗人的诗人:罗智成、杨泽、鸿鸿、谭石、陈克华。
台湾现代诗的卓越代表:郑愁予、林泠。
此外我还想说的是,我没读到许多重要诗人的诗作(或数量远嫌不够),比如余光中、洛夫、叶维廉、廖威浩、白
杨牧先生,他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咋舌。最近读了《疑神》,他是否伊朗霍梅尼之类人物?他未在群分之列。
商禽的诗,洋溢着生命的意味,人世的忧苦,有如宋词中的小令。他正是如孔子说常忧患的那种人。鸟啼花落皆与人通,正由于对人生及诗的十足忠实,掺杂了大量非理性因素,渊乎其莫测也。——却有更大的真实。这便是诗的真谛吗?
商诗以真纯感人(《无言的衣裳》美极了),少有对功业的向往及恢宏气象,此为弊端乎?而劳逸之态各殊,更显心明而力定。
夏宇以丰富的内心经历过剩的智慧咄咄逼人。她对命运似有超常的理解力,她本来便生活在常规世界之外,那世界近似于艺术世界。再加想像的活跃、元气的充盈、语言波俏而犀利——恰如古人“开千枝花一本所系”之谓。她生来是为了写诗的——除了写诗还有什么更好玩的呢?可她隐瞒着,此所以善藏其拙乎?却时时巧乃益露也。
零雨小姐的诗深具阳刚之美。她常常陷入沉思中。是要寻找摆脱这个世界的途径吗?是为了沉思而沉思吗?仅仅为了审美吗?她似乎苦苦地寻求着一种本源,一种高过物质岁月的东西。那东西就要抓住了,千钧一发又滑脱了,于是下一首重新出发。我们模模糊糊感觉到了却难以命名。是生吗?是爱吗?是东方哲学的核心“道”吗?然而禅心清妥语无烟火,她的虚静令人着迷。她肯定发现了我们未曾发现的东西,所有的意义都在那儿了。——这是否便是艾略特所谓的“非个性化”?她的全部努力只是找到客观对应物吗?
有时她的过份执着令人苦恼。我多么希望她再前进一步:向无限的光明,顶礼!
我有个顽固的成见,诗要别才,因此学士大夫难为得阃奥者。——正由于此,我并不太喜欢歌德和艾略特。
痖弦和梅新因其名望影响以及诗坛领导者的地位,与这一情境大致吻合。说到诗人,我常常把他俩忘掉了。
袁枚说:“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世之行万里历险艰者,固有无加于诗之人,又何以不可加于诗耶?可见这念头是偏颇的。
五十年来,痖弦诗极可能是中国最有力度最富想像的诗。他以玄学派的方法抽象地思考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拥有远距离把握对象的能力,拥有创意。——假如将诉诸客观的笔触更大程度地转而指向感觉即心理——不是对像如何是看上去听起来如何——再增强一点胆气——老来颓唐之胆气——痖弦诗本应成为中国现代诗之范本及康庄大道。他为什么不继续写呢?是嫌诗之功用太间接太迟缓了吗?
梅新与痖弦风范截然不同。他不像痖弦如此注重才气和巧智,他于技术似全然不顾。娓娓道来如毛毛雨落入心田,令人疑惑:诗人本性若此?抑或大巧之拙?是富家雕金琢玉然后竹几藤床乎?让人读不出一丝矫揉一毫造作一语虚言一句妄语,却因真而达悄邃之境,常至于我们熟知的诗歌领域之外。诗人的猎犬在那儿奔驰,捕捉到的是出人意料的感受不可捉摸的情思,来龙去脉几近迹灭。
《在桔子树下》《云》《自然》惟性之所宅也,若马之不羁也。这里是否有诗是什么的道理?——各个方向无限扩展的道理?
罗智成、杨泽、鸿鸿、谭石、陈克华似已形成台湾有教养有才华有希望的学者型诗人群。他们的学养丰厚,底力充沛,有道气,与俗违,于作诗做人皆取法乎最上,胸中有物,囊有余资,为诗坛之中坚无可置疑。
他们的具有创新的和坦率地实验性的诗作正为中国现代诗寻找着方向。最可贵处在于,他们拥有相当有份量可以明确辨认的思想(作为学者比作为诗人还更成熟些)。且不在乎艺术反艺术,敢于走极端,无视审美性质,无视传统。更由于禀赋、学历和勤奋,拥有透视历史与人生的力量。
罗智成诗中,诗与哲学青黄杂糅精色内白。他善于征服最重大题材,极具感性,主题复杂,却写得既庄重又随便,举重若轻,气度雍容。
杨泽与谭石都是要入世行道的。在那里,“诗言志”不是方针而是本性。他们敢于对世界和历史进行哲学性把握。诗并不是目的,仅仅是一种方式。才气也成为次要的了。我们感受到的毋宁是一种心境一种情绪。诗只是副业,具有“无用”的性质。与他们心向神往的未来始终维持着一种角度,这是极令人称羡的。
陈克华仿若弗洛伊德的门徒,企望着大慈大悲。他关心的是意识层面的爱意与敌意之下,在生命暗无天日的底层到底是些什么痛苦骚乱和憧憬。——美与邪恶大约兼具。真理太严酷了。他执着地宣示它们,让所有人都觉得烦恼,也觉得欣悦,觉得宽慰。原来根源便在于此呀。或许本该如此。人可能获得彻底解放吗?可能自由吗?姑且试试吧。——我这样猜想他。
他向诗的原则大举进犯。无论思想,还是感情。西方哲人说,诗没有原则。——我喜欢这个原则,我断定他也喜欢。
我惊异于鸿鸿内心世界的纯净无邪。在这种心情中办事或写诗多么愉快呵。但那单纯已是经历了磨难、失望、求索之后的单纯。——惟思之精,屈曲所以超迈也。既然苦为四圣谛之第一谛,为什么不像鸿鸿那样玩玩呢?《小红帽》真好,是人类的情绪和诗中之极品。要紧的便是这种精神,这是精进之路,由此方到禅定,取得大智慧。——问题在于玩得开心吗?诗人的重负对于二十九岁的生命来说是太沉重了。我推崇他绚丽的才华,在明快的诗句下却看到凝聚的精血,总觉欣喜又忧郁。
轻快地哭泣轻快地笑轻快地写诗吧,鸿鸿,时间还早着那。
我总以为,别指望四十岁以前把诗写得如何如何,这要求太严峻了。诗不是青年人的事。——是中年人的事。——假如保持着生命力的旺盛和观感的活跃,诗是五十岁以后的事。干嘛着急呢?
林泠的诗是属于东方的。尽管在当代,在中国,很少有人比她更能领悟西方文化的神髓。
那诗是阴柔的,女性的。——是足以抗衡这个强大世界的。
那不是某种思想,仅仅是一股灵气。在岁月的流逝中,它靠什么保留下来的?以至可以想见千秋过者,犹祀其像?我不明其妙。但那意绪那情怀确乎是活生生的,通过另一世界的灵光而感应着人间。
不信就看《雪地上》或随便别的什么,其虚空若列子之风。莲塘诗话载初白老人云:诗之灵在空不在巧。看林泠之诗令人不能不信。——那写法是须借助神力的。
《易·咸卦》象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余谓为信然。
在现代诗中,将物质与精神比重作如是和谐安排的郑愁予——和拉斐尔有相似处。几至可望而不可即之境。
我每每感佩于郑诗的知性,纯粹而又纯粹,光鲜而又光鲜。——从不掺假,是来自天性吗?——我相信确乎有一种天生的诗人。
以横贯东西之学,禀承诗人天赋和六十年心灵历程(那是何其丰富的历程),自由地而又自在地推动了两个时代的现代诗运动,又如此元气淋漓,如此圆融,郑愁予外,似无二人。
诗歌不是竞技,这话只对了一半,诗歌也是竞技,这就圆通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诗是否拥有更大能量?如何继续蜕变?既然唯变是适,郑诗之平衡如何打破?在那个神鬼莫测的非理性领域,理应存在更大魔力,如何采掘呢?——这也许只是一个完满的终结?未来如何开始?
一个时代是否只有一位最大的诗人?
我们可否假定是我们自己?——这是不是诗的最高原则?——人的最后幸福?
艺术世界是一元的吗?是多元的吗?是多元基础之上的一元吗?
中国现代诗优势何在?如何与西方诗比一比上下?症结在哪里?
大陆诗人可否适应台湾诗坛的氛围——把桌子搬到台湾写作?
台湾诗人适宜于在大陆写吗?
这样可否弥补彼此之不足?在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意义上实现横向杂交?
在《现代诗四十年》庆典上,女诗评家奚密呼吁:为诗歌保存一方净土。——这首先需要公平——诗的标准的公平,权衡的公平——出乎意外的公平。
不懂怎么公平呢?怎么叫懂呢?
必也正名乎,要到什么时候呀!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