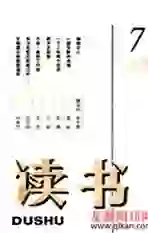温柔,不需要声音
1990-07-15痖弦
痖 弦
四十年来,台湾的散文逐渐发展成一种内容丰富的文类,风格多样,作家辈出,建立了自己的形式特色和语言系统,这跟西方现代文坛比较不重视散文的情况,恰成对比。
而这些年来,大陆散文发展的进程,由于海峡两岸长期的隔离,我们所知甚少。最近,读了刘湛秋的散文集《雨的四季》,又参阅了一些大陆散文家的作品,发现两岸散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大陆现代散文的成长虽然一度受到十年文革的
以刘湛秋为例,他对散文提出的美学主张,如:现代意识的追求、表现手法的创新、感觉与情绪的侧重、在语言上诗化的倾向等等,都跟台湾散文家经常强调的完全相同。这种在文学上分头发展却殊途同归的情况,可能是来自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现代散文的传统——许地山、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梁实秋、梁遇春、陆蠡与何其芳,这一连串中国散文史上发亮的名字,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热源。
刘湛秋也是个翻译家,对于域外文学的广泛涉猎,使他具有辽阔的世界现代文学视野。但在他整个的散文世界里,并没有感染到现代主义的晦涩与不必要的欧化语言,在内容上更是一派中国情调及非常朴素的田园风格,基本上,是承自我国南方文学秀婉气质的一种作风。作者生长在江南的水乡,所以,写水特别见功夫。在他笔下以河为路、以船为家的水乡生活,每每可见佳篇。如写月光下的小河即有如此动人的笔致:“在有月光照耀的地方,呈现出一条白色的玉带,像河中之河——那么,船驶进了那条月光的河,会到月亮中去吗?”而水乡的少女则是“粼粼的水”所浇铸出来的。她们的歌声在河上荡漾,“波纹的唱片慢慢的旋转,一圈圈,把那甜甜的秘密旋进河的深底。”这些描写不禁使我想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的确,他们都是最了解水的作家,文章的语言也一如清澈的水,鉴照出作者的心影。在本书中,作者写溪、写河、写湖、写海、写潮及船与龙舟的文章很多,所以他自己说:“是水哺育了我的文学思维。”面对着水的时候,作者的创作力显然特别旺盛。他不只是诠释岁月如流的惋惜和喟叹,而是在“情思万千、浮想联翩”中找出人世的变与常、生与灭;所以他不仅是在写水的形貌,同时也在试着创造一套属于他的“水的哲学”。
除了秀丽的江南水乡,作者的足迹也遍及了北方大野。他笔下的北方是粗砺的、荒寒的。就像艾青那样,他体会到北方广大土地上悲哀的忧郁,但他的态度却是安静的、冥想式的,不同于大乐章那般属于抗争的、激情的,而是一种室内乐式的静静宣叙。他看到卖花生的妇人露宿街头,只说:“啊,可爱的夏天,伟大的庇护者,你提供了多么大的旅社,既不收房钱,又不要证件。”简短的几句白描,可以看出作者感情的深沉,有时候反而胜过了捶胸顿足的呐喊。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田园诗人的静观。当他漫步在凋零的森林,走过荒芜的田野,乘坐一连数日夜隆隆不停开向远方的火车,总也不忘在山水自然与季节运转中体会人的处境。生、老、病、死,一如植物的枯荣,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辩证。面对着“落叶如潮,秋风如梦”,作者靠着简净的散文语句来诉说四季的奥秘更替,也找出了“处置自己”的方式。他的作品多半都是喃喃独语式的,面对大自然,他常常是表面写景,实际写情,从情景的溶会,阐明缘起缘灭的宇宙规律。不过,他的这一切描写都是透过现代人的感受来表现;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山山水水早已有古代的骚人墨客题
感觉与情绪的着重、语言的诗化、形式的创新,应该是刘湛秋散文中企图追求的标的,在本集里处处可见作者这般的用心。当他看到林中的一条小路忽然隐没了,他说那隐没的小路“像一支没唱完的歌曲”。写“一朵血红的蔷薇”,则说“开在我们别离的时候”。形容孩子的泪,他说:“仿佛是一颗星,最漂亮也最温暖的一颗星。”写太阳:“太阳像可爱的小鸟,在每一棵树上都筑起小巢。”写他那只活了一千多天便死去的妹妹:“后来,我再也没有了妹妹,但她在我心中,跟我上学、工作,她长成了大姑娘。但是我不愿她跟我往前走,那样她会逐渐成熟,甚至衰老。”写他自己躺在帆布椅上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头上,是绿色的浓荫,蝉声和着远方的溪水”,而“战争正在书本中狂热的进行”、“战争的血腥几乎把书染红了。”这些段落的描写,有的显示出作者锻字炼句,的功夫,有的显示出作者的性情与气质,使读者和作者之间产生一种默契与会心,使这册散文集成为一本很温暖的书。
在本书当中,许多情景的描述都相当优美,但偶尔有一两句属于价值判断的文字,若是可以再加转化,或许可以收到另一种意在言外的效果。此外,全书篇章多半过于短小,有些题材似乎可以再扩大深入发挥,但却有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予人“未完成”的感觉。这大概是受到随笔体例的影响,比较接近于冥想录的写作方式,而不同于一般散文在篇章上的刻意经营,多少有点不够淋漓尽致。但是作者笔下那种大陆性的朴素、辽阔气质,与悠邈的气氛,颇令我想起屠格涅夫所著《猎人日记》里的俄国乡下风情。而这些正可弥补台湾一些散文作品在文词上的过于雕琢乃至矫情的瑕疵。另一方面,如果作者在撰写时,能提高张力、增加戏剧性的安排,或许可以展现出多样而和谐的风貌。笔者不谙散文,对于此中甘苦较少体会,以上的建议,纯粹是一种直觉的印象,或许一得之愚,有当于作者之心。
两岸文学交流以来,我跟大陆作家在书信、稿件上往返的前辈、朋友很多,有一部分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如:冰心、巴金、沈从文、萧乾、赵清阁、许杰、施蛰存、吴祖光、端木蕻良、柯灵、骆宾基、卞之琳、辛笛、袁可嘉、冯亦代、苏金伞等人。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的作家来往得更多。同本书作者,彼此可说神交已久,只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碰面。我知道他生于一九三五年,安徽芜湖人,他只比我小三岁,我想,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他主张建立中国的“轻派诗歌”,而我呢,也有关于“轻文学”的思考与评议。他是俄国大诗人普希金著作的翻译者,而我早年也是普氏作品的爱好者,并且曾经手抄过他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一九四七年,希望社出版,吕荧译)。他翻译俄国革命前夕诗人叶塞宁的作品,而我也深爱叶诗,对于叶氏的自杀一直未能释怀。
多年来,本书作者与我之间唯一的联系,是诗、是对于文学共通的梦。当我吟哦着他《等待》一诗中的首段诗句:
在那些困惑而沉垂的日子里
等待像天空微弱的星星
它朦胧,但发光
它遥远,却又像在身边
我不但体会到他所说的“盐一般的苦味”,我也感受到,梦想之所以成真,就如他诗中所说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顽强地等待。”
从本书作者所在的北京农展馆文联大楼到台北四维路的寒舍,希望那距离不是迢遥的。
〔《雨的四季》,刘湛秋著,台湾汉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