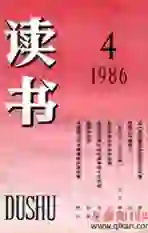“以史证诗”的剖视
1986-07-15钟元凯
钟元凯
唐宋以来,人们一直用“诗史”的称号赞美杜甫的诗歌,认为这是伟大作家所理应享有的最高荣誉。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却对此提出了否定性的质疑。在他看来,“诗”与“史”是“异垒而不相入”(《诗广传》卷五),“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一
在中国,很早以前人们就习惯于把诗和史勾连起来,用史家的眼光来读诗和解诗。诗和史就其各自的本质而言,它们之间原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史的主要功能在于“载事”,孔子说过:“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而诗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又常常是“缘事而发”的。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诗言志”里的“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其较早的字义是“记忆”和“记录”(《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一册)。在先秦典籍里,就有不少关于某诗缘于某事的记载。例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了郑子产执政期间“舆人”的先后两次诵诗,内容从诅咒转为颂扬,表现了民心的显著变化①。同书宣公二年载宋师败绩,主将华元逃归,巡城时守城人唱的歌也显然是讽刺这位被俘赎回的败将的。②这些风谣都具有很强的“缘事”色彩。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风行“列士献诗,庶人传语”的政治讽谏,人们出于讽谏的需要,更是有意识地把“诗”和“史”勾锁在一起。讽谏需要引古证今,也需要采用诗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某些格言警句,诗和史同作为加强讽谏雄辩性的手段而打成一片。如《左传》僖公二十四载:“郑伯……不听王命,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
但这种批评风气之大开,则始于汉代,其代表便是对以后产生了权威性影响的《毛诗序》。《毛诗序》上承孟子的方法又进一步使之系统化和具体化。它在提出“讽渝美刺”的诗教理论的同时,又由此出发具体地解说“诗三百”,使之和周王室盛衰演变的史迹一一加以对号坐实。按照它的证说,国风和大、小雅均可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美文王、周公之政教的,另一部分则是刺幽、厉等衰世的。继《毛诗序》的示范张扬,“以史证诗”的方法遂告正式成立。
有很多因素促成了这种批评的眼光和方法。汉代的文化学术思想为政治上的功利主义所统摄,“主文谲谏”被强调为诗赋文章的主要职责。批评家既视诗为讽谏工具,那么说诗时自不免要联系史事,诗中本有史迹的不妨申说之,诗中本无所谓史迹的亦不妨附会之。而史籍中一些述及诗的本事的材料,又正好为其张目并提供了方便,如《尚书·金滕篇》载周公赋《鸱
《毛诗序》之后,随着诗教理论的深入人心,以史证诗的方法也愈益为人们所重视和乐于采用。尤其到了宋代以降,诗教说取得了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演示这种方法的实例也就不时出现在诗格诗话一类的著作里。例如,被称为“熙宁新学”代表作之一的王安石的《诗义》,在解说《诗经》时完全尊信《毛诗序》,“以序囿诗,以诗殉序”。(参阅邱汉生《诗义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不难看出,以史证诗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政教的轴心展开的。换言之,对诗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功用的考虑,始终是这种批评方法赖以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每当文化上的功利主义思潮抬头时,这种方法也就获得了新的势头。由于这种关系,使它与生俱来地具有某些可贵的素质,也带来了许多先天的不足。
二
诗和人类的一切精神产品一样,都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只要我们不把它简单地视作是某种自生自灭的封闭体,就没有理由不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它。何况许多优秀的诗篇,本身就包含着闳深的历史内容。屈原在《离骚》、《天问》中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兴亡成败的历史经验。杜甫更是自觉地用诗肩负起“辨人事”、“明是非”、“存褒贬”的庄严使命,他在诗中屡以太史公自比,如“尉佗虽北拜,太史尚南留”(《送王信州鉴北归》)、“南图卷云水,北拱戴霄汉;史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等;有意以史笔为诗:“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对于这些诗人的这类作品,以史证诗不啻是揭示其丰富意蕴的有效的阐释方法。尤其是对那些处在特殊处境下,以隐晦曲折的手法寄托对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看法的篇什,这种方法更时有抉隐剔微、发人耳目的妙用。例如陈沆的《诗比兴笺》卷二,就是通过对阮籍所处的政治环境的考察,从三个方面揭橥了阮诗的“遥深之旨”,即:“悼宗国之将亡”、“刺权奸戒后世”和“述己志(忧时或自励)”。对背景的全面把握,使他在探寻阮诗形象深隐的喻义时颇多胜解,能发人之所未发,如云“‘金石离伤,明翻云覆雨之易;‘丹青明誓,慨托孤寄命之难”等等。在这里,以史证诗不仅道破了诗人的隐衷,而且还有助于读者体察到阮诗所特有的、寓沉痛巨哀于嘲讽之中的情调。可见,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能昭示和发扬诗歌创作中的社会批判精神,而正是这种批判精神,构成了古代文学遗产中“民主性精华”的核心。
但传统的“以史证诗”,其失误之处也斑斑可见。这些失误表现在几个方面的简单划一:在诗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其视野往往只局限于政治一隅,把诗歌简单划一地都视作是朝政兴衰的直线投影。在诗的内在生命方面,往往无视或者漠视诗人情感生活的全部浓淡色彩,把诗情简单划一地视作是某种政治评判。在诗的表现和传达方面,则把丰富的艺术处理方式简单划一化,视图解式的隐语为最普遍最有效的表达手段。批评家既然以为诗歌只是一种保存了若干史迹的文献材料,那么,批评的最高目标也就在于把诗还原为史实。由此出发,对诗歌本事的勾沉就成为第一要义,背景足以涵盖一切、说明一切,诗本身只是一种复述,说诗者如果能字字句句牵合以求义理之所安,批评也就得到了圆满的完成。从把诗降格为文献资料开始,最后以批评沦为烦琐的章句之学而告终,传统的以史证诗的一系列失误,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顺序接二连三发生的。
以史证诗的批评家通常遵循“由外及内”的工作程序,即首先从收集背景材料的“外证”着手,然后根据某种先验的道德律,预先拟定诗人在如此这般情势下应该有的、正当的态度和倾向,最后再到作品中去寻找“内证”,即诗中意象、典故和用语的影射义。这种头脚倒置的行走方式,常常淆乱了批评家的视听,使他们陷于非常可笑的境地,例如《毛诗序》把许多描写男女风情的民歌都披戴上峨峨高冠、褒褒朝袍;沈德潜把汉乐府《有所思》中失恋女子的决绝之辞,说成是“人臣思君而托言者也”;陈沆把《上邪》中情侣间的海誓山盟,也说成是“忠臣被谗自誓之词”,等等。他们都把人类情感世界一幕幕情趣盎然的活剧,改造成清一色的廊庙朝堂。诗人们常常被这等供奉搞得啼笑皆非,无怪乎他们要提出抗议说:“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李商隐《有感》)了!方法上的迷误还常常会弄巧成拙,把严肃的批评庸俗化,甚至堕为恶解。如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之七:“糁径扬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末句竟被某些人解作嘲诮杨贵妃、安禄山淫乱事,故王夫之愤愤地斥之为“市并恶少造谣歌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死矣”(《
如果从思想方法上考其失足之由,就在于批评家忽略了把诗与史关联起来的“中介”,这“中介”就是作为创造主体的诗人,就是诗人千差万别的创作倾向、个性和追求。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对于诗歌而言,“重点不在当前的对象而在发生情感的灵魂”(《美学》第三卷第三章)。诗人作为人的个体存在并不只具有政治品性,他还拥有七情六欲,诗的全部魅力正产生于这种丰富性之上。把诗的表现局限于一隅势必导致其雷同化,导致其生命的萎缩。即使是那些具有强烈社会政治意识的诗人,他们所写的一些“缘事而发”的作品,也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复述,而是在传达他们的思索和感觉,传达他们内心的回响和反应。离开了对“中介”的把握,则“外证”和“内证”尽管言之凿凿,都不免成为无根臆说,成为某种精致的赝品。以史证诗的歧义每由此而生。史料愈是丰富,解说却反而愈见驳杂和迷乱,批评家自以为引证所谓“信史”便是实事求是,殊不知缺乏“中介”的事实本身就并不可靠。在考察文学现象上和社会现象方面一样,“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因为那样做,“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二十三卷第279页)
说到底,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是一定文学观念下的产物,它的效用和价值,取决于它所赖以产生的文学观念的成熟程度。传统的以史证诗的方法,毕竟是在文学观念尚欠发达、尚未完全独立的时期建立起来的。这种方法的长短得失可以概而言之曰:明于考“史”而京
关于“诗史”的那场公案引起了我们以上这一番跋涉。回过头再来看王夫之的那几句话,似乎更加耐人寻味。王夫之强调诗、史之为“异垒”,当然不是要在它们之间人为地强分畛域,他倒是清醒地看出了传统批评中一个已经为人们所习惯了的谬误,看出了这种谬误可能会给创作带来的不良后果。当人们在强调诗和史的联系时,常常有意无意地轻忽了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而这种疏略会导致一个严重的过失,那就是把诗的批评标准“非诗”化。正如他所反复申言的:“史才固以
①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②歌词原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