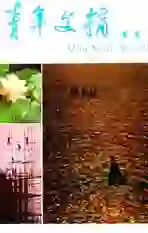在时代的炉膛里燃烧
1984-11-01李旦初
李旦初
凡是能够拨动人们心弦、点燃人们智光的好诗,都是诗人内心燃烧的结晶。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好:“真正的诗人却是身不由己地怀着痛苦去燃烧自己并点燃别人的。”
这三首借“煤”咏怀、托物言志的短诗——郭沫若的《炉中煤》,朱自清的《煤》,艾青的《煤的对话》,都堪称“燃烧自己并点燃别人”的杰作。
对“女郎”唱着恋歌的“煤”
《炉中煤》是郭沫若《女神》集中的名篇之一,作于1920年一、二月间,上距五四运动七、八个月。诗人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这里说明了此诗创作的时代和主旨,也透露了作者在创作中如何“燃烧自己”的信息。
《炉中煤》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诗人火一般的激情,同时也来自表达这种激情的独特方式。全诗洋溢着真挚、纯洁、强烈的爱国之情,激扬着恳切、急迫、刚烈的报国之志,给人以高尚的情操,振奋的力量,而构思之巧,设喻之妙,又可谓前无古人,后乏来者。诗人以正在熊熊燃烧的“炉中煤”自喻,并将它拟人化而为诗中之“我”,以“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象征“五四”时代朝气蓬勃的祖国,通篇即以“炉中煤”的口气,向“年青的女郎”倾诉衷肠,一唱三叹,以抒写“我”“眷念祖国的情绪”。
此诗的比喻,不可以一般修辞法视之。它是诗人构思的基点,抒发感情和理想、创造形象和意境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提供了优美的物象——“煤”对“女郎”的深情热恋,而且提供了感情至深的意象——“我”对祖国的赤胆忠心。读这首诗,需始终抓住这两个方面,潜心品味其丰富深远的象征意义。
诗的第一节,先写“女郎”对“炉中煤”的“殷勤”,已暗示“女郎”的进取精神和高尚情愫,即她对于光和热的恋慕、追求。因此,“年青的女郎”所象征的中国,也不是平常的中国,而是诗人所理想的“美的中国”。再写“炉中煤”对“女郎”的“思量”,思量至深而“燃到了这般模样”,形象地点明了“我”和祖国的亲密关系,把“我”的一颗赤子之心和盘托出;而“我不辜负”一句又隐含以身许国之意。
第二节写“炉中煤”向“女郎”表白身世,由躯体的燃烧写到“火一样的心肠”,将热烈的情爱升华到纯净、坚贞的崇高境界;象征的意蕴亦深化一层,把“我”对祖国披肝沥胆的高尚情思抒写得淋漓尽致。“卤莽”一词,既准确地写出了煤的特性,又生动地写出了“我”的个性、气质及其无法控制的感情冲动。
第三、四节写煤“原本是有用的栋梁”,过去长期“活埋在地底”,如今“总得重见天光”。这里象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包括“我”在内的无数有志之士,有用之材,受到压抑、埋没,爱国有罪,报国无门,只有把个人的悒郁,民族的忧愤,深深隐藏在心底;如今既已“重见天光”,“我”将如“炉中煤”,燃得通红炽烈,给黑暗的人间以光,给冷酷的世界以热,自己化为灰烬,在所不辞。至此,由“炉中煤”这一形象所体现的“我”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理想,便发挥到了极致。
“炉中煤”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熔物的特性、“我”的气质和时代精神于一炉,写“煤”之燃烧,即抒“我”之激情,亦即抒人民之情、抒时代之情。这就是此诗之所以引起人们强烈共鸣的奥秘所在。
《炉中煤》的艺术形式同它所抒写的情思十分和谐。它是一首比较严谨的格律诗,章法、句式、韵律都很讲究。从章法看:全诗四节,首节总述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第二节侧重抒爱国之情;第三节侧重述报国之志;末节与首节取复叠形式,前后呼应,将全诗推向高潮。从格式、韵律看:每节五行,每行音节大体均齐,一、三、五行押韵,一韵到底;而各节均以“啊,我年青的女郎!”一声亲切温柔的呼唤起唱,造成回环往复的旋律美,诗情随诗律跌宕起伏,韵味深长。
《炉中煤》不愧为爱国诗中之绝唱!
在火园中“跳舞”的“煤”
朱自清的《煤》作于1920年1月9日,与郭诗同时。
抒写诗人追求光明、向往美好未来的情思,是朱自清初期诗歌的主旋律,此诗亦然。全诗仅十六行,分三个层次:先叙煤堆积于地,因“腌臜”、“黑暗”而使人们厌恶、惧怕;次述煤在炉中燃烧,“透出赤和热”,“美丽而光明”;再写人们对于煤的赞美。这里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以人们对煤先后截然不同的态度,造成强烈的对比感,抒发诗人在风雨沉沉的黑暗社会中看到光明的无限欣喜之情。
朱诗所写的“煤”,也是一个“黑奴卤莽”却有着“火一样的心肠”的美的形象,但其意蕴却与郭诗不同。这个“黑裸裸的身材里”“透出赤和热”、“美丽而光明”的形象,究竟象征什么?可以有这样两种理解:一、它象征“五四”时代新思潮;二、它象征俄国十月革命。因为二者都有这样的特点:当它尚未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时,人们都视之如洪水猛兽,憎恶之,惧怕之,避之唯恐不及;而一旦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人们便转而亲近它,赞美它,为之载歌载舞,欣喜若狂。
然而,朱自清不是郭沫若,他自有其独特的“燃烧”方式。因此,朱诗与郭诗相比,各有特色,风格回异。朱诗咏“煤”,亦取拟人之法,不过不是将“煤”化而为“我”,而是化而为“你”。诗人站在客观立场,用第二人称写法,把“煤”比拟为一个有着高尚情感和优美姿态的舞女,写煤在地下堆着是“你在地下睡着”,写煤在炉中燃烧是——
一会你在火园中跳舞起来,
黑裸裸的身材里,
一阵阵透出赤和热;
呵!全是赤和热了,
美丽而光明!
这和郭诗的区别是非常显著的。郭沫若的《炉中煤》是借咏物诗形式而写的抒情诗,朱自清的《煤》则是地地道道的咏物诗。郭诗重主观抒发,物我一体,物即是我,“煤”的思想感情即我的思想感情;朱诗重客观描述,物我有别,物中有我,我的主观感受渗透于对煤的客观描绘之中。郭诗直抒胸臆,形成奔放、热烈的浪漫风格;朱诗托物寄兴,形成含蓄、朴素的写实风格。郭沫若所代表的浪漫诗派同朱自清所代表的写实诗派的分野,于此可见一斑。
从沉默中爆发巨响的“煤”
在郭沫若、朱自清两位高手的咏煤之作问世之后十七年,青年诗人艾青又以不同的音调唱出了咏煤新声:《煤的对话》。
此诗作于1937年春。时值抗战爆发前夕,祖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人民与日俱增的抗日情绪,正酝酿着一场时代的大风暴。诗人敏锐地预感到时代脉搏跳动的频率,开始“拂去往日的忧郁”,以极大的热情去讴歌“曾经死了的大地”的“复活”(《复活的土地》),讴歌中华民族的觉醒。
“人类的歌,是最丰富的歌,最多变化的歌”。艾青深谙此理。他决不重复别人的构思、别人的意境,决不模拟别人的语言、别人的声调。同样是写煤,同样用拟人手法,同把煤创造为象征性形象,艾青与郭沫若不同,也与朱自清有别:他既不用第一人称写法,由“我”直抒胸臆;也不用第二人称写法,对“你”娓娓叙谈;而独辟新径,用第一、二人称巧妙结合的写法,以“你”“我”对话的形式,一问一答,四个来回,以仅有十二行的短小篇幅,创造了一个意蕴深广的巨人形象。
这个“巨人”的形象,是古老的中国的象征,是已经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个形象,概括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深重的灾难,赞美了它伟大的灵魂,无穷的热力,预示了它神圣的抗争,灿烂的前景——庄严的文明古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地火在运行;伟大的亿万人民的心灵里,怒火在燃烧;残暴的侵略者必将葬身于火海,光明的新中国必将在火海中诞生。这个形象,凝结着时代的精神、情调和气氛,人民的忧患,意志和希望,诗人的怨愤、信念和理想,三者熔于一炉,闪闪发光而聚于一个焦点:崇高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力。
诗人的歌,就是这样丰富多彩:同样是写“煤”,各有各的气派,各有各的格调,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旨趣,各有各的感情燃烧方式。郭沫若写“煤”,创造寓刚于柔的美的形象,给人以爱国的情操;朱自清写“煤”,创造优美的形象,给人以向上的情操;艾青写“煤”,创造壮美的形象,给人以民族自信的情操。这种情操美,来自人民生活,经过诗人的感受、体验、提炼、酿造,显得更高、更美,更能陶冶人的性情,美化人的心灵。郭诗潇洒而热烈,于缠绵情调中透出刚劲之气,使人焕发青春活力,保持赤子之心的真率;朱诗清丽而蕴藉,于天真格调中闪现哲理之光,使人热爱生活,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艾诗深沉而雄浑,于抑郁情思中溢出昂奋之志,使人振作,保持永远进击的姿态。诸如此类的美感作用,都是超越时代而永不衰竭的。
(王凯风摘自《名作欣赏》1984年第1期)
附: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
郭沫若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啊,我年青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要我这黑奴底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啊,我年青的女郎!我想我的前身原来是有用的栋梁,我活埋在地底多年,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啊,我年青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选自《女神》,泰东图书局1921年8月版)
煤
朱自清
你在地下睡着,好腌臜,黑暗!看着的人怎样地憎你,怕你!他们说:“谁也不要靠近他呵!……”一会你在火园中跳舞起来,黑裸裸的身材里,一阵阵透出赤和热;呵!全是赤和热了,美丽而光明!他们忘记刚才的事,都大张着笑口,唱赞美你的歌;又颠簸身子,凑合你跳舞底节。
1920,1,9,北京
(选自《雪朝》,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版)
煤的对话——AY.R.
艾青
你住在那里?我住在万年的深山里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你的年纪——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比岩石的更大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年代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年代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选自《旷野》,生活书店1940年9月初版)